69书吧>一个故事50字 > 第 102 章 碾碎涩青梅十一(第3页)
第 102 章 碾碎涩青梅十一(第3页)
说是笔筒,其实原身是一个玻璃啤酒瓶,用切割机切开,再打磨干净,切口处圆润如翡翠,虽是玻璃,因是林格手工课上亲手做的,在兄长心中的价值也价值连城。
同样的浓绿色的玻璃,精雕细琢成造型新异的细长颈大肚花瓶,插着香气怡人的白茉莉,灯光下垂着莹润柔光。
即使是视野开阔的白日,也燃着灼灼的明灯,擦得亮闪闪的银质刀叉,白如雪的餐巾折成玫瑰。
林格无心用餐,她还沉浸在失恋的难过中,对杜静霖那些俏皮话完全提不起兴趣。
对方可怜兮兮地说实在找不到同行者,又感谢林格愿意陪他过来吃饭。林格不想扫朋友的兴致,他说什么,她也耐着心去听,去聊。
事实上,等喝完最后清理口腔用的气泡水,她已经忘掉了刚才交谈的一切。
杜静霖问她将来打算上哪所学校——他自己已经被父亲安排好了,去国外镀金,学出些本事,再回来继承家业。这个苦恼的小少爷,目前最大的困扰,就是即将和国内的好朋友们告别,几乎是孤零零一人踏上异国的征程。
林格想了很多话来安慰对方,就像她,父亲还在服刑,妈妈生病,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家庭中,她还爱上了可能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喔,最后这句话不能讲,这是她的秘密,将来死掉后也要带入陵墓中的东西。
痛下决心选择放弃爱情的女孩,在杜静霖那奢侈的苦恼和单纯注视下,连“身在福中不知福”
的批评都说不出了,她只能故作轻松,双手托着脸,笑嘻嘻地告诉杜静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杜静霖会结交到很多好朋友,坦坦荡荡的前途就在眼前;
她也会好起来的,舍弃了一段不伦恋,今后尽是大道。
这种难以言表的忧伤,在两人离开这个高档餐厅后被燥热的风烘干。又暗又闷的空气更像一个蒸炉了,在这沉沉的、辨不清方向的天地之中,唯独马路对面静静地站了一个人。
白色的宽大T恤,黑裤子,背着一个老旧的双肩包,正在路边的小店前买东西。他个子高,头顶上方不远处就是店铺的招牌,红彤彤,像一盏高悬的灯笼,字体印刷端正,炒货干果铺。
人群中,他的身高太惹眼,躲都躲不掉,更无忽略的可能性。
林誉之。
林格想了很久,才记起,林誉之提了一句,说他今天下午去见朋友。
没想到这么巧能碰上,她叫了一声哥,林誉之回头看了眼她的方向。两人离得太远,不辨面容,只看林誉之微微弯腰,从那窗口中拎出一纸袋,缓步
往他们方向来。
杜静霖没再说送林格回去的话,人家哥哥来了,他刚才喝了点儿红酒,有点上头,脸都是红的。大约真的是酒精上头,不知怎么,看着林誉之过来,他没由来想起他爹揍他的场景。心一慌,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不礼貌了,急匆匆说句“我有点事”
,即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捂着脸,不想让林格的哥哥看到自己现在酒蒙子一样的红脸,也有着不可思议的胆怯。
林格没拦。
她不喝酒,刚才也只小小尝了一点,浅尝辄止的范围,颊边却有红晕,很淡很淡的一抹,像碾碎了花瓣拖曳出的汁痕。
近乎忐忑地鼓起勇气,她率先叫了一声哥。
林誉之给的回应很轻,自然地递来手中的塑料袋,甜甜的香,一纸袋的糖霜山楂球,褐黄色的纸,雪白糖霜,殷红山楂,圆圆滚滚的几粒,:“你同学?”
轻描淡写的疑问。
“是杜静霖,”
林格解释,“你认识。”
“喔,”
林誉之点头,“你好朋友太多,刚才没记起。”
电动车停在不远处,天色愈发暗了,沉沉的,店铺的灯,路旁的灯,深浅不同的黄和白。林格低着头,不敢看林誉之,她并没有良好的自控力,也无优秀的理智。
他的身体有幽幽的干净味道,这种气味并不是来源自衣服或者洗护产品。林格抬起手臂,鼻子凑到手腕处,用力地嗅了几下,不一样,和哥哥身上的有着微妙的相似。
好朋友曾提起过,说林格闻起来很像学校湖边亭侧月季花,林格闻不出,人对自己的气味往往都不怎么敏感。
可哥哥的味道空前的清晰,像那天林格好奇去闻月季花味道,不小心捏碎的几片叶子。
能够解渴的清凉味道。
一想到共同香味的源头,林格眼睛更酸了。
忽而,一双大手抚上她的眼睛,几乎是将整个脸都罩住,林格呆了两秒,仰脸看,颇有些不知所措:“哥。”
“晚上喝酒了。”
不是疑问句,肯定的语气。林誉之微微皱着眉,不过几秒,又舒展开:“上次不是和我讲,不乱喝酒么?”
“……就喝了一点点,”
林格说,“套餐里附带着两份,不喝也是浪费。”
“浪费,”
林誉之波澜不惊,“如果今晚他订了酒店的房间,对你来说,不去也是浪费?”
!
多梨向你推荐他的其他作品:
希望你也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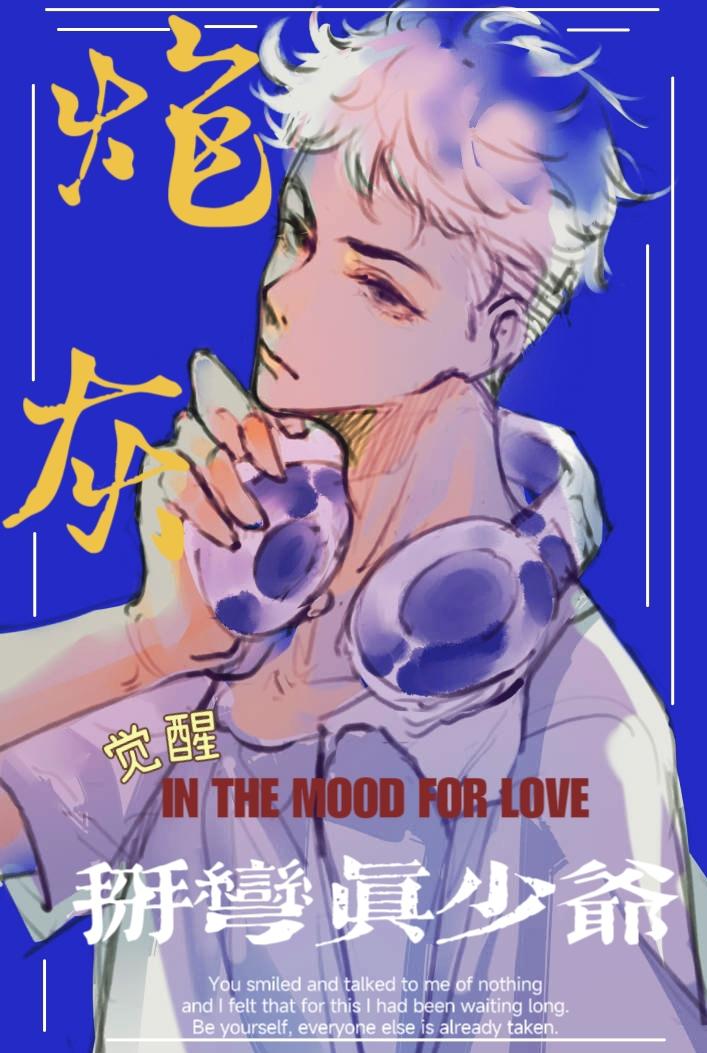
![[综英美]跟着红桶学做人](/img/1784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