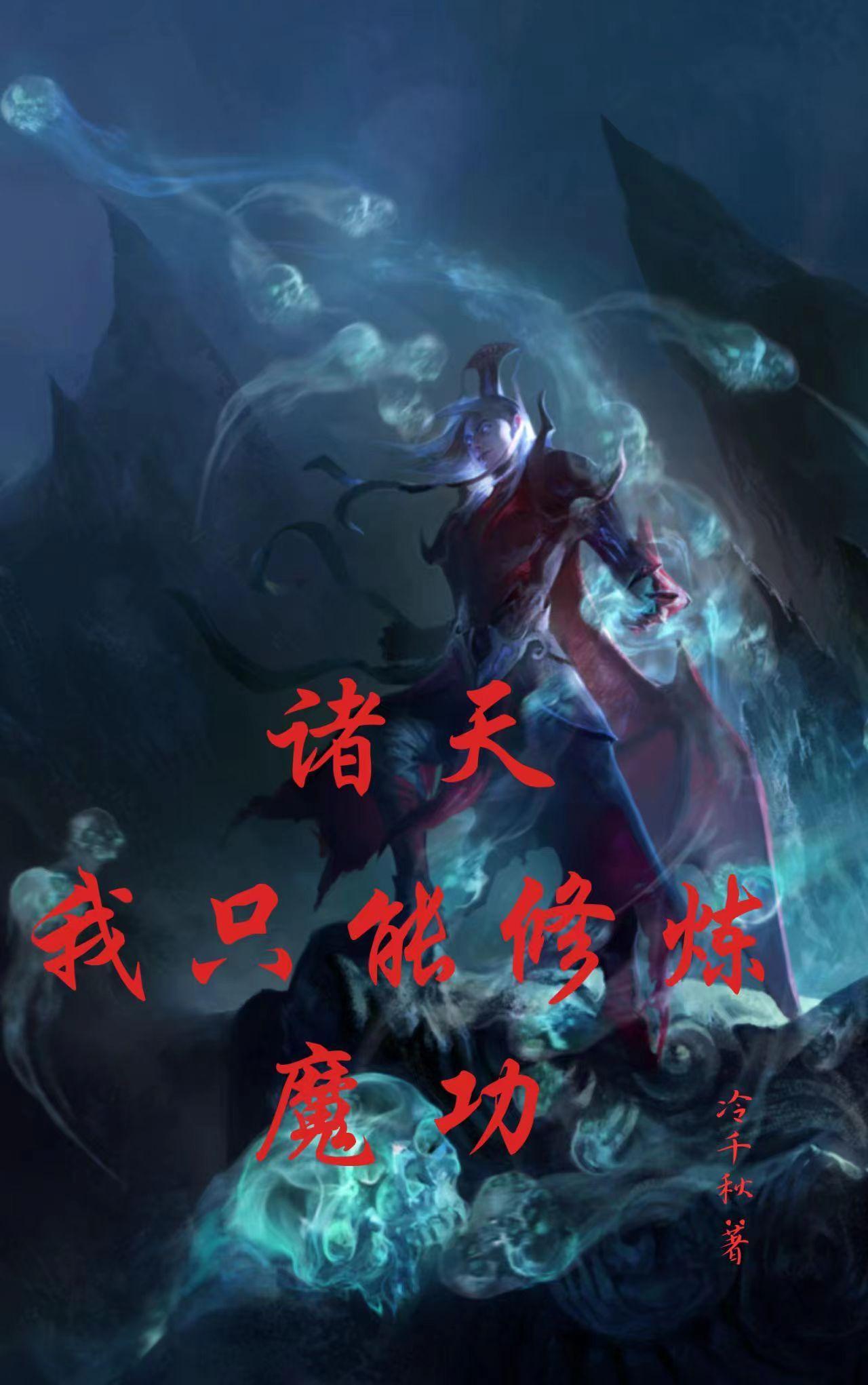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太子他不肯和离在线阅读完结 > 第41节(第4页)
第41节(第4页)
谢煐回道:“由曹御史辅佐,他有过单独赈灾的经验。户部的人被平王撇下,并未被抓,待我过去还能继续用他们。”
怀伤沉吟道:“曹御史虽与二王派系都不亲,却是个圆滑之人。目前来看,青州出事必涉平王,天子想来也知道,选此人前往,还是有保平王之意。”
谢煐淡淡地道:“我不去便罢,我既去了,多少也要扯下他一层皮。”
小会议开到这里,各人散回去做出发准备。
谢煐临走时对怀伤道:“我留一千东宫卫在京中,全听先生调遣。”
怀伤看看他,又看看安静跟在他身边的白殊,笑道:“殿下两年前便能临危不乱、力挽狂澜,如今身边再添一大助力,相信此行必能圆满。”
白殊跟着谢煐回前院,小声地问他:“殿下没将白泊叫我过去的事告诉他们?”
谢煐脚下略略一顿,随既状似自然地道:“事忙,忘了。”
白殊盯着他直视前方的眼睛,忍不住扬高唇角,却也没说破,只转个话题道:“我在想先生刚才说的第三种情况。先前白泊说天子会派你前往青州,他却想将我留下,我曾怀疑过是不是他也牵扯进青州事中。可现在看,却又不像。”
若是青州那边是白泊在推动,白泊既想留人,那提要求之时完全可以只提谢煐一人,不需要把白殊也带上。
谢煐瞥过一眼:“白泊在密切关注青州事态。这次他如果不是因为父子亲情想留你,那真正目的便是想分开你我。”
白殊一口断言:“绝不可能是父子亲情。他面上演得再像,我都没感受到他对我有一丁点的关心。”
两人默默走了一段路,待到岔路口,谢煐突然从袖袋中摸出一块墨玉牌递给白殊。
白殊接过细看,发现一面雕着龙,另一面刻有个“煐”
字。
谢煐道:“此乃我唯一信物,见牌如见我,你可凭它调遣所有东宫卫。”
白殊微愣——东宫卫可是谢煐保命的底牌。
“跟在我身边。”
谢煐凤眸深幽,“希望你不会有用到它的一日。”
六月十三清晨,谢煐带人前往青州治疫。
十艘大船从码头缓缓驶离,旗舰桅杆上高高飘扬起黑龙旗。
text-align:center;"
>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