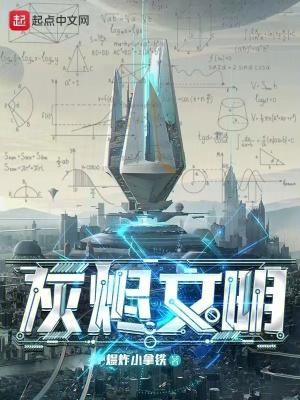69书吧>欺负清冷仙尊gb > 第27章(第2页)
第27章(第2页)
但上面还糊着一层草药,似乎又有人给他止过血。
二丫看到这个情况,吓得停止了哭泣。
一时之间空气凝重下来,似有千斤压在两个小姑娘的肩膀上。
段轻羽见她们被吓到,忙说:“不要紧的,已经不疼了。”
二丫擦干眼泪,瘦小的脸上前所未有的认真:“段哥哥我们带你去医馆。”
凤来却踌躇了,“二丫,我们没钱。”
想到钱,二丫充满斗志的眼睛一下子黯淡了,是啊,她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帮段哥哥呢,可她几乎没有迟疑:“我可以给他们干活,求他们给段哥哥治病!”
段轻羽有些感动,他和两个少女不过萍水相逢,何必让她们为难。
他身上的绳子已全部解开,可双脚使不上力气,想撑着站起来却失败了,仓库里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东西。
他喘了口气问:“你们看到应寻了吗?”
二丫满脸愤怒,挥舞着拳头:“我当然看见啦,就是那个坏女人把你害成这样的!”
段轻羽怔住,下意识地否认:“不会的。”
“怎么不会!”
二丫气得又要哭起来,越急越说不出话。
凤来帮忙解释:“二丫亲眼看见那位姑娘拿着带血的刀,锁上仓库的门,而且我们来的时候门锁都是完好的,也没有破坏的迹象,应姑娘……应该就是害你变成这样的凶手。”
她的语气中有小小的不确定,因为她不敢相信一个女子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丈夫。
“对!而且她已经消失三天了,肯定跑掉了。”
二丫抢着说。
段轻羽抿起嘴,眼皮垂下,遮住了大半的情绪。
在昏暗的不吃不喝的清醒三天里,他想了很多。
昏迷前最后的意识,是应寻递给他水喝,甚至于这段时间他总是在晚上喝过水后立马睡去,原来是她给自己下了迷药。
从前不肯相信,这一刻似乎得到证实。
可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后这样对待他?他们不是伴侣吗?
或许根本不是伴侣。
“仇人”
这个词十分合时宜的出现,盘旋许久,不曾消除。
他仍想问应寻要个答案。
“你们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你还管她!”
二丫不满地嚷嚷着,“那个坏女人死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