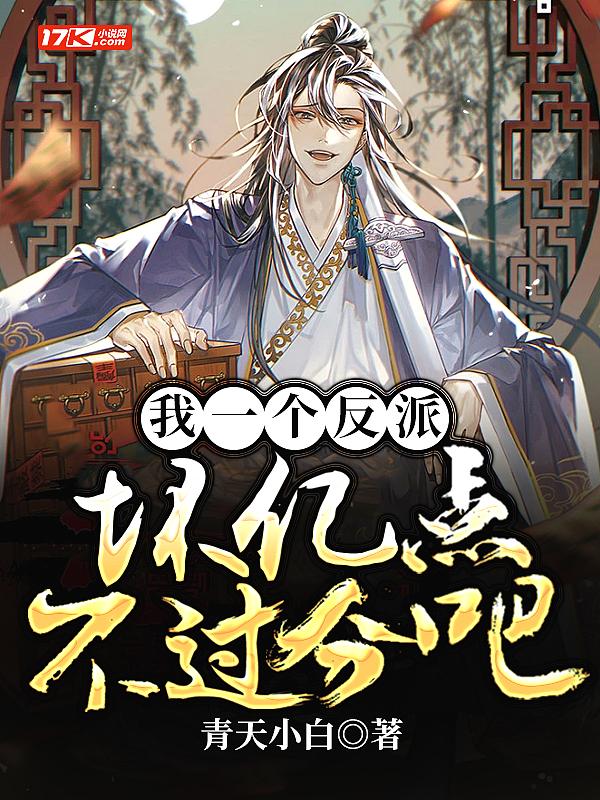69书吧>咒术回转伏黑 > 第77章 列车向前(第2页)
第77章 列车向前(第2页)
我有想问的话,我有需要知道的信息,比咒灵味道更重要,事关我家人的存亡。
“那个脑子什时候找上的你?”
相似的问题,在机器猫台灯前其实问过,但那个时候,他很多地方没有说实话。
夏油微微蹙了一下眉,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正常来说,应该都是迟缓一下,给出回答。而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错开话题。
“你那件武道馆的衣服丢哪了?出门的时候,我不记得有帮你装起来。”
我拉过身边的纸袋,眼睛没离开他,手却在身边摸,胡乱搅两下,揪出那件衣服,扔在了桌上。
他下意识的摸了一下鼻子,把桌上的衣服拉到自己的怀里,“原理,把你装衣服的袋子给我,我帮你都叠好。”
他还是不愿说。
我们俩对于彼此的真实用意,不会迟钝到连一点苗头都感受不到。
他知道,他知道我要问的问题,我想要了解的东西。
而我也知道,他不愿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把纸袋递给他,他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然后看似心平气和的把衣服有序叠好,但他的手不稳,好几次都没拿住衣服。
列车在向前,要进入一段隧道了。
窗外的光骤然暗淡,轰鸣声如蒙在罐子里时,我说,“犬路红染死的时候,27岁。”
夏油杰头也不抬的说,“才27啊,也太可惜了。”
“可惜吗?假如,她不是被杀,而是自杀。你也觉得27岁,很可惜吗?”
对于永远活不过18的我来说,我不懂,为什么可惜。
“因为人生很长啊。至少要活到八十吧。”
他又想了想,改口,“不对,至少五十。”
他改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咒术师并不是一个能够长寿的职业,但是【因为人生还很长】这句话,我不理解。
“自杀的人,会因为人生很长而放弃自杀吗?自杀的人,不就是因为人生那漫长的痛苦看不到头,才会选择结束的吗?”
他顿了顿,说,“或许是这样。但真的很可惜啊,人生那么长,万一还会有希望呢?”
我思索片刻,换了个角度,“八十岁的老人要自杀,他会因为人生还很长,万一还会有希望,就放弃自杀吗?”
夏油皱眉,“这不能比,你在偷换概念。八十岁,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那十五岁自杀的人,人生就不算是尽头了吗?”
他听到我的话后,叠衣服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整个人都无比僵硬。
我慢慢往后靠,让身体贴合柔软的椅背,我想让我的话变得柔软一点,“人生的尽头,只有自己能看到。尽头什么样子,尽头在哪个节点,只有个人可视,个人可选。旁人就算一时干扰,也不能真正做主。”
“所以,就只能旁观吗?”
一直沉默的人,忽然开口问我。
我缩进座位上,想到了原因,想到了那一世又一世,想到了山上的墓地,想到了那只对我闭合的病房大门。
“我们只能面对。”
因为唯有面对,才有机会释怀。
列车的闷响在淡出我们的听觉,隧道有限,只要向前,终能离开。
在微亮的月光照进来时,衣服袋子被重新放回了桌上。
我想,他或许准备好进入那段不愿面对的回忆了。
关于神奈川,关于十五岁恐山鸣柏的自杀,还有关于那颗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