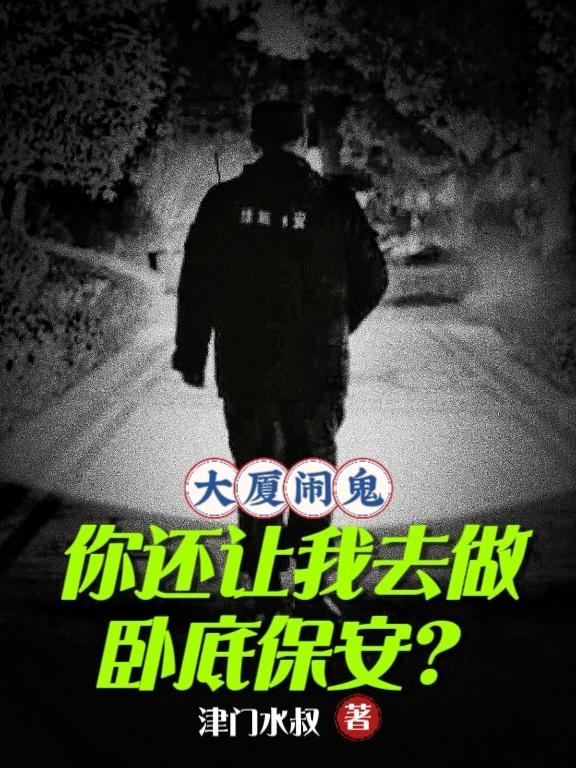69书吧>死无罪证豆瓣评分 > 第二十二章 捕蝶网22(第2页)
第二十二章 捕蝶网22(第2页)
傅亦道:“没事。”
覃骁见这俩人你一言我一语旁若无人的样子,大吃飞醋,甩着胳膊嚷道:“我就知道你跟我分手的原因没那么简单!什么叫生活方式不同啊,全是借口!你看上别人了吧你!这大叔!就你!你他妈一大把年纪了还上赶着给人当小三——”
“覃骁!”
杨开泰一双墨笔勾出来的眼睛瞪圆了格外有气势,连傅亦都为之一震,那个耍酒疯的帅哥也撇着嘴没了动静。
杨开泰怒道:“注意你的言行,看清楚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覃骁:“三宝儿——”
杨开泰:“你先回去吧,我会找时间和你说清楚。”
覃骁像个被主人抛弃的大狗一样,蔫头耷脑一摇三晃地走向自己的跑车,留下一身酒气。杨开泰看着他摇晃的背影不禁有些担心,担心他出了车祸死在路上,于是向傅亦请假,把酒鬼送回家。
傅亦允了他一天假,让他把问题解决完了再上班,要不警局门口堵着个大男人,也不好看。
杨开泰和覃骁走后,傅亦独自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其实刚才杨开泰并没有做错什么,然而傅亦的语气却过于严厉,他对覃骁的滋事有所不满,但是绝对没达到动怒的地步,至今他仍想不明白那天晚上他为什么会生气。
车窗忽然被敲响,傅亦看到杨开泰隔着车窗冲他笑。傅亦打开车门,等他上了车坐在刚才妻子坐的副驾驶座上,又把两扇车窗全降了下来。
杨开泰拿着两盒冰淇淋有些疑惑地看他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打开窗户,这样一来冷气就全散了。虽然想不通,但杨开泰没问,他还记得覃骁冲撞了傅亦,他需要代覃骁向傅亦道歉,于是把左手的冰淇淋递给傅亦,说:“吃冰淇淋,傅队。”
傅亦接过去,发现杨开泰手背上有一道擦伤,手腕处也有些泛青,再抬头看杨开泰的脸,他颧骨上也有点伤,脖子上一道瘀血一直延伸到锁骨,再往下就被T恤领子遮住,看不到了。
傅亦拧着眉问:“你身上怎么有伤?”
杨开泰含着木勺正在撕冰淇淋的包装,闻言不以为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后视镜扳下来看了看自己的脸,把勺子从嘴里拿出来,说:“嗯,我和覃骁打了一架。”
傅亦静静端坐在驾驶座,觉得自己不应该再问了,杨开泰和那个男人的关系已经被他知晓了,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保持旁观者不闻不问的态度才是最不会出差错的。但是他又感到了和昨晚如出一辙的埋伏在心底的鼓噪,一时竟很难把那些心绪抚平。
杨开泰低着头挖冰淇淋吃,吃了几口,忽然说:“你看出来了吧,傅队。”
闻言,傅亦扭头看向他,只见他脸色平平地低头挖冰淇淋吃,但是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傅亦很不想承认,无论出于何种角度他都不想承认,但是此时又不得不承认,于是说:“很平常,你不用担心,而且我不会说出去。”
杨开泰垂着眼睛看着丝丝冒冷气的冰淇淋,轻轻笑了笑,说:“说出去也没什么,我家里人都知道。”
傅亦不禁愣了愣:“你——”
“我出柜了。”
杨开泰倒是很爽快很洒脱,“高考完第二天我就出柜了,家里人还挺支持我的。我爸妈,我哥,我姐,都不反对,我还挺幸运的。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出柜后都被逐出家门开除祖籍了,我出柜的时候我家里人挺平静的。我妈还说她早就看出来了,因为我打小就没正眼看过女孩儿,反应最大的是我爸,被我妈敲打敲打就拧过来了。我姐还帮我介绍对象,昨天来单位闹事的覃骁,我们俩就是在她组的局上认识的。”
傅亦道:“是覃厅长的儿子?”
杨开泰点头:“嗯,但是他爸特烦他玩这个,覃厅长觉得男人在一起就是乱玩儿。前一阵子就把他弄出国想戒掉他这个坏毛病,我就索性跟他分了。”
他忽然抬头看向傅亦,笑容腼腆,“我跟你说这些,你反感吗?”
杨开泰的眼神太透亮太澄澈,像一泓未染世俗的净水。傅亦觉得自己接不住这样的目光,于是转过头直视前方,把已经开始融化的冰淇淋放在一旁,抽了一张纸巾擦着手淡淡道:“不会。”
杨开泰松了一口气,把他当作知心大哥一样,挖着冰淇淋接着说:“他挺好的,圈子里很乱,找一个踏实的很不容易,他对我也挺用心的,我跟他分手不是因为他爸,也不是因为跟他不清不楚的那些人,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我天生是gay,而他不是,他是在上流社会中待久了,什么妖魔鬼怪都见过,也全都泡过。当初他对我献殷勤,也只是想泡我,但是时间久了,他认真了,我不知道他能认真多久,他的生活里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各种各样的诱惑太多了。我不认为我能让他喜欢我一辈子,所以就早些了断比较好。”
“那你身上的伤?”
杨开泰笑容明亮又爽朗,说:“我要分手,他不同意,说来说去说不通,就动手了呗。他打不过我,我身上只有皮外伤,他的一个膀子被我卸了,哈哈——”
他的笑声短促而清脆,因为太过愉快所以显得刻意,笑了两声后,脸上的笑容急速消失,唇角牵引的弧度刻在脸上,显露出僵硬而苦涩的意味。他怔了一会儿,又说:“说实在的,我还是挺喜欢他的,当初着急寻找真爱,谁对我好我就跟谁好。好了这么久才发现他对谁都好,所以我不能再跟他好了。其实我完全可以继续跟他好下去,但是我——”
杨开泰察觉到自己情绪有些失控,埋下头竭力稳住哽咽颤抖的声调,像是恼恨自己般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傅亦觉得自己有义务安抚杨开泰,比如给杨开泰一个拥抱。但是他什么都没做,和杨开泰相比,他身上还有更大的义务。妻子舒晴,还有女儿,就是他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车里的冷空气早就散光了,此时车窗大敞着,源源不断滚进来的热流和源源不断涌出的冷气在打架,车里的温度忽冷忽热,让人身上热一阵,寒一阵。傅亦浑身的皮肤冰凉,但他的血是热的。或许是杨开泰的悲伤传染了他,让他回想起他在和杨开泰差不多的年纪里那些狼狈的记忆。他从山呼海啸般的哭喊咒骂声中逃出家门,那天的阳光燥热,空气稀薄,一双铁手扼着他的喉咙险些把他的脖子掐断。他跪在地上狂呕,像是五脏六腑都坏了,心肝脾肺肾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得吐出来才行。最好把那彷徨无助的灵魂也呕出来。
然后,穿着长裙的邻家妹妹走到他身边,帮他把嘴边的秽物擦干净,对他说:“我们结婚吧。”
一个星期后,他们登记结婚了。走出民政局,他看着手里鲜红的结婚证书,忽然觉得红色背景下的那个男人不是他,笑得那么卖力夸张,拼命保持和其他人同样的姿态。他也是头一次发现自己笑起来其实并不好看,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表达欢欣喜悦都是点到为止一笑带过。
傅亦把车窗合上,从驾驶台上拿起一盒烟,抽出一根点燃了,也不抽,静静夹在手指间,看着那个光点从生走向死。
杨开泰闻到烟味,转头朝傅亦看过去,从内到外都放空了似的看着傅亦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也把目光放在傅亦手里那根正在燃烧的香烟上。
香烟燃烧的速度很快,光点后留下一段扭曲而完整的烟灰,摇摇欲坠,像蛇蜕下的皮。光点和烟灰连接处忽然微微颤动,杨开泰有所感知般摊开手掌伸到烟头的下方。脆弱得风吹即断的烟灰以一种痴男怨女投湖跳崖般绝望的姿态往下掉落,即将落到杨开泰手上时,被另一只手掌截和。
傅亦抓着那半截滚烫的烟灰,微微皱着眉头,往掌心里塞了两张纸巾胡乱遮盖住被烟灰灼伤的掌心:“接它干什么?”
杨开泰眼睛里迅速闪过一片凌乱的散光,抿了抿干燥的下唇,说:“可是,快掉到你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