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书吧>升斗小民出处 > 第231章(第1页)
第231章(第1页)
时间悄然而逝,转眼便是暮秋之际,北疆战鼓已然擂响,喊杀声之下俱是累累白骨。而烽火烧不到的西南,在潭州牧不懈的努力下,西南夷终于松口,答应与大燕通商,但通商地点只限于潭州治所。
北疆的战事愈演愈烈之时,都城的来信也到了潭州治所。
庾浚看罢来信,沉吟不语。
秦黍见状便轻声问缘故。
庾浚将手里的信递予她看,秦黍接过,片刻之后,她面色凝重,低声道:“怎会如此?”
庾浚并没有解答她的疑惑,只是道:“蓟州旧部已有人听诏去了北疆。圣上如今圣体不便,朝中怕是人心不稳。”
“那可如何是好?”
秦黍有些不安。
庾浚面色凝重,他背手而立,目光一直落在北边都城的方向。
寒冬之际,雪色遍及潭州。都城的密信带着北疆的消息而来,胡虏已退至漠北。这一战,胡虏大伤元气,部族青壮死伤殆尽,因着严冬,粮草不继,部族中老弱又死伤一批,如此一来,内乱便生,也再无余力去大燕相抗。
但随着北疆战役落幕,皇帝重伤的消息也暴露于朝野,一时间朝中人心激荡,众议四起。
庾滉在密信中特意提起,让庾浚领兵回都城。
“回都城?”
秦黍面色有些难看,知道朝中局势的她自是知道这一趟回都城的凶险。
庾浚颔首,他看着秦黍,目带关切,道:“我此去都城尚不知祸福,你明日便离开,去秀州。”
秦黍皱眉,下意识不愿,她刚欲开口,便叫庾浚抬手止住,他的脸上是不容置疑的肃色,秦黍心知他决断已下,想让他回转心意怕是不易,于是不再多言。
庾浚并没有耽搁,翌日便带兵北上。只是适逢严冬,河道结冰,水路不畅,整支军队只能走陆路。
这日刚扎营休整,庾浚便听底下人来报,“后面有马车跟着,斥候来报已经几天了。”
庾浚不觉有异,听罢皱起眉来,“既是连着几日了,怎么不叫人驱赶?”
部将为难,苦着一张脸看着自家将军,“……是夫人。”
……
背风坡处,简陋的扎营之所,秦黍叫人带过来之时,目光所及之景便如是。进了帐,围拢在篝火之处的几位部将一见着她来,忙起身朝她拱手行礼,而后便告退离开。
“此行还不知结果如何,你何须跟着我?”
庾浚手拿枯枝挑着面前火堆,眼睛也看着面前火堆,并没有望向她。
“你我夫妻,自是一体。”
秦黍走到他身旁,蹲下,也看向面前燃烧的莹莹篝火。
静默片刻,庾浚长叹了一声,“罢罢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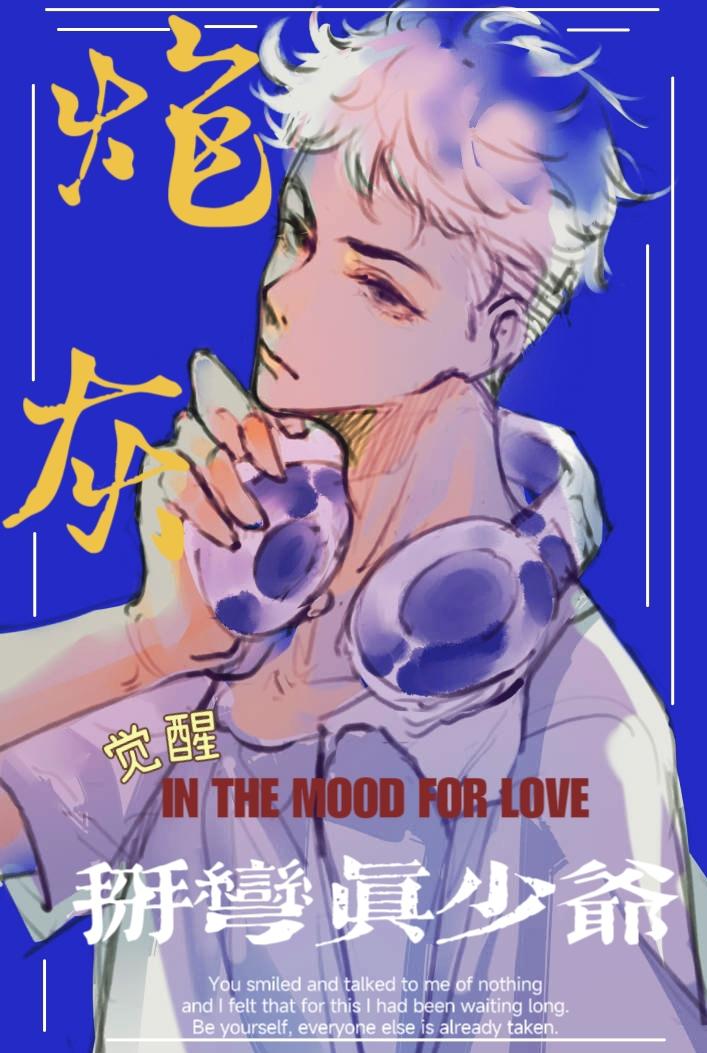
![[综英美]跟着红桶学做人](/img/1784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