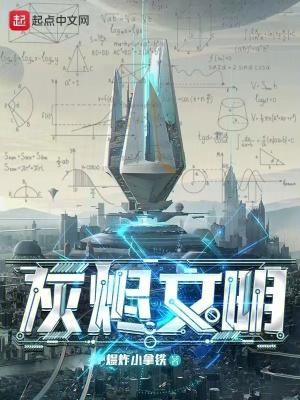69书吧>丧夫后竹马他回来了百度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后来,她就算受了天大的委屈,再大的欺负也不敢往家里说。爹爹为了护住他们兄妹三人,拼命往上爬,而她也不想因为自己,再连累她的哥哥和父亲。
起先她只是一个人默默蹲在角落,挨下无数拳脚也死不吭声。到后来,是卫遥帮的她。
此人性情顽劣,偏偏侠骨仗义,天不怕地不怕。卫遥能打的时候,就把那些人往死里打,到后面遇上打不过的十几人,他就挡在她的身前,撑下了全部拳脚。
如今温画缇回想起来,对他当年义气仍然怀有感激。
既然如此,这四回的春风一度,也权当报答他昔年之恩吧!此后再别无相欠。
禁锢
眼见事情瞒不住哥哥,温画缇只好进了屋,把一切如实告之。
哥哥听完沉默良久,既想骂卫狗,愧疚之情却更浓烈。
他摸摸妹妹的头,丧叹,“是哥哥太无能了,遭难之际救不了家人,现在还要别人来救,更是连累了你。”
“哥哥不要这么说,我们是骨肉至亲,谈何连累不连累的。”
虽然父亲只是芝麻小官,虽然哥哥壮志难酬,不曾仕途高就,虽然她常常因为出身太低被人嘲笑但她从未不觉得他们是累赘。他们是这世上最爱她的家人,宁宁也是这世上最可爱的小妹。
哥哥突然又想到一件要紧事。
只是这件事,太过尴尬。甚至他自己还没娶妻,稍稍一想就不知所措。
最后,他轻咳两声,还是得跟妹妹提个醒,“咳你今早服过避子汤吗?等父亲回来,咱们也要离开了。你如今名分上还是范氏儿妇,那卫狗又对你纠缠不休,万一到时候怀了”
看他纠结这么久,温画缇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她拍拍哥哥的肩,颇为轻松:“没事,小事一桩!哥哥忘了吗,我嫁给范桢五年,整整五年,我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可见我天生与子嗣浅薄,这几次,应当也不会有差。”
哥哥想了下,“万一是范桢自己不行呢?”
说到这,温画缇也有些尴尬,脸莫名发烫。范桢行不行,她可是太清楚了——她想起无数日日夜夜,两人就像对水中鸳鸯,旖旎缠绵。范桢他可太行了,温柔又细致。
只是有件事,温画缇还不曾告诉过别人——成婚后的第三年,她和范桢出游,来到五神山时,曾经向一位归隐的高人询问子嗣的事。
其实子嗣的事,不单是她婆母着急,连她和范桢都很急切。为什么他们这么相爱,却连一个交融两人血脉的孩子都没有。
那高人,人称华佗再世,有枯骨生肉之能。他先是帮范桢看过,又帮她诊脉。最后告诉他们,是她在子嗣上福薄。若是上苍垂怜,这辈子就能有一个。若是不垂怜,或许膝下孤寂到老。
她和范桢听完都有少许失落。但很快,范桢就安慰了她,“没有也无妨,都是命数罢了。大不了我们从叔伯那儿过继一个来。”
后来回去,范桢只让她将这件事瞒住,就当没听过,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所以如今哥哥的担忧,对温画缇来说一点事都没。
她甚至大胆地,无所谓地想——反正这辈子很难生出一个,若是不小心有了,未尝不是老天对她的垂怜?
那是她的骨肉,是她的家人,她一定会独自,把孩子好好养大。至于它的父亲是谁,根本不重要,它也不需要知道。它只要有母亲,有疼爱它的外祖一家就够了。
树林分别的时候,温画缇就没有在颍郡久待的意思。
她来,不过是为了确定哥哥和小妹是否还活着。
今天到了她和长岁约定的日子,长岁会来接她回京城。所幸她带来的东西本就不多,简答收拾一下包袱,就能出发。
临别前,温画缇对哥哥和小妹说,“你们别担心我,我去京城把最后一些事办掉,马上回来接你们。到时候爹爹也回来,咱们一家就离开这里,找个地方重新过日子!”
宁宁不舍地抱住她的腰:“阿姐,你要走多久呀?”
“放心,要不了几天的。”
温画缇与家人辞别,一想到将要面对的崭新生活,心中雀跃不少。
她步伐轻快地走向大门,却在此时,被一众护卫拦截。
“温娘子,您不能走。”
“为什么?”
温画缇疑惑且不满地看他们:“我又不是这儿的人,我要去哪儿我自己说了算!”
护卫面无表情道:“这是将军交代的,您不能踏出这个门。”
眼看温娘子就要跟他们跳脚,有个机灵的护卫忙出来调和,“别吵了别吵了!温娘子,您若要出府,不妨请个将军的意思来?将军一直在书房里,若没有将军的口令,我等是万万不敢放您出去。”
温画缇知道他们也不过是听命令的,不欲多为难,擦擦拳就去书房找卫遥了。
此刻卫遥正在桌边写着什么,她经过窗户瞥见,那似乎是大红的雕花纸,不免让她想起与范桢的合婚庚书。
等到她敲门进屋,却见卫遥飞快把那东西收了。他瞥她一眼,语气很冰凉:“你来找我做什么?”
温画缇听那语气,显然他今早的气还没消。男人们,不就最在意袴下那点尊严?
她几乎想笑出声,良久世家命妇的训练却让她忍住了,心里只剩痛快。
温画缇绷紧脸,直言道:“你下达个口令吧,我要出府。”
卫遥冷着眼看她,“出府?你为什么要出府?”
“我要回京城。”
她没有解释行踪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