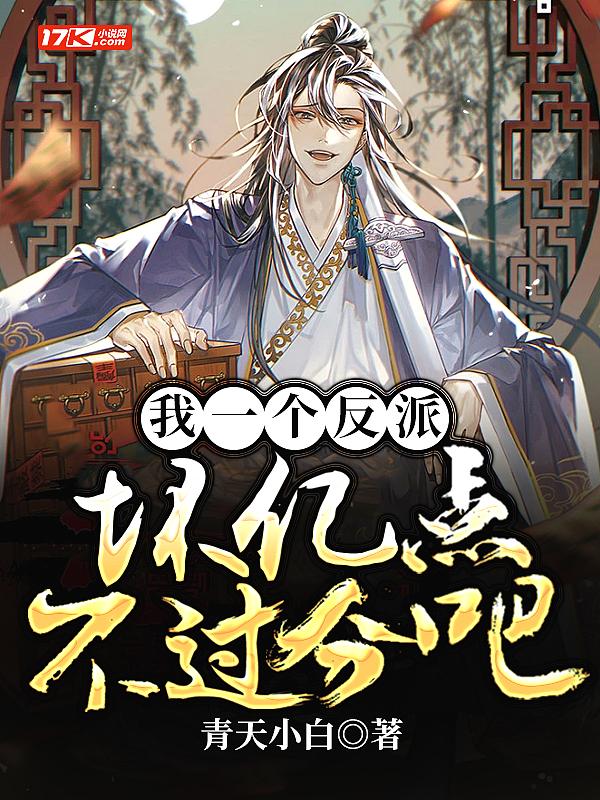69书吧>小道姑一身反骨 番外 > 第66章 雀人7(第1页)
第66章 雀人7(第1页)
五年前,林长贤用“办事不力”
的理由,将县内河工的工钱全都扣下不发,导致河工无钱可收,纷纷回家种田。
日积月累,河道淤堵,一年后的汛期,大水无路可走,遂成了洪水,造成房舍损毁、农田被淹、农作物牲畜损失无数、灾民遍地……
陈南山听得义愤填膺,一拍惊堂木:“你所说的,有何证据?”
“县内数十名河工的名册在此,大人可以派人将他们找来问个究竟,还有,户房、工房之人应该都还记得,大人不妨一并问问。”
李昱白难得情绪外露的冷哼一声:“好一个克己奉公、勤俭爱民,混账!”
四年前,将林长贤滞留盐官县,失去回京都当官机会的洪水,原来不但是天灾,还是人为。
若只是为了贪墨的银钱,那真是丧心病狂。
林长贤这人,究竟还有什么秘密?
林父和林二弟面对这些控诉目瞪口呆。
林父颤抖着反驳:“不,绝无可能,我儿子一片丹心,只想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我儿子出身贫寒,知道老百姓的艰难,他绝不会……”
“我儿子在祖宗面前发过誓,赴外就任后一定会好好当官的。”
“这些丧良心的事,不可能是我儿子……”
“噗……”
这位老父亲一口血喷出,竟气得差点晕死当场。
“大人所说的,某不敢信,”
林二弟,“父母亲在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不是不知道,他怎么会……贪墨的那些银钱呢?难道给了嫂子娘家?我就说,嫂子只怕是伪善,要不这么多年,怎么看不到任上回的银钱?”
“我就说么,自大哥在任上成亲之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都是女人之祸……”
“胎记?我哥身上没有什么胎记,要说的话,他脸上有个不甚明显的狗屁疤。”
“狗屁疤就是,就是那种不黑的也不长毛的,反而比其他肌肤稍微白那一点点的一小团,不仔细看,或者不是家人,压根都看不出来。”
林长贤的脸,也被烧得干净。
这火啊,真懂事。
……
才刚当上知县不过六天的吴明瘫成了一摊泥。
“还想着糊弄走本官是吧?”
陈南山将衙门内众人的供述一本一本的扔在他脸上。
“不说也没关系,抄你家的人已经在路上了,一来一回快得很。”
陈南山笑起来,“你说不说,都不影响抄家砍头,至于能不能给你家留根香火,本官也不在意。”
吴明:“大人饶命,小人认罪,林大人确实有份私账,就在他卧房内,由夫人收着,应该是烧没了,但……但小的偷偷的记了一份,数目应是差不离的。”
“小的愿奉上账本,只求能饶我儿一命。”
李昱白一点都不意外,平铺直叙地问:“正院那把火是谁放的。”
吴明:“小的不知,但不是小的放的火。”
李昱白:“这些年贪墨的银子,去了哪里?”
“启禀大人,每个季度末,总有个自称是林家仆从的老者,带三四个人,乘夜挑着空担子来,天不亮挑着实担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