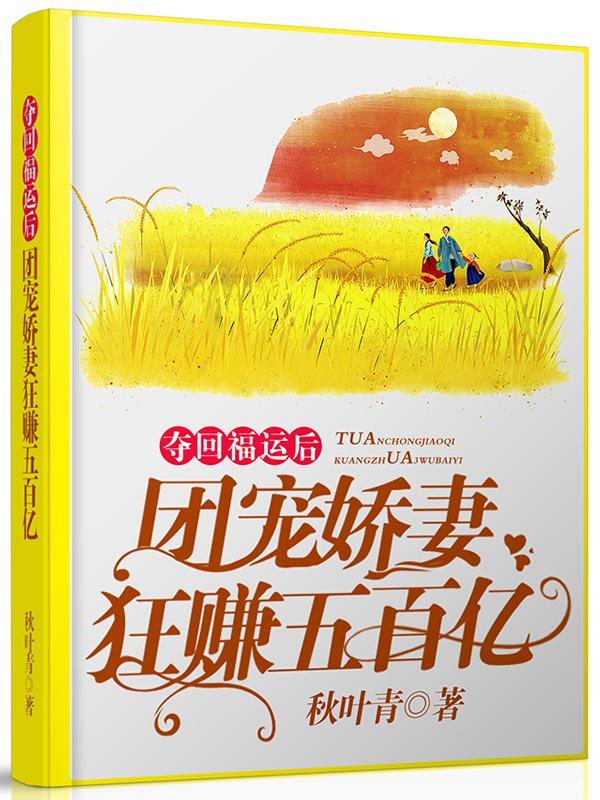69书吧>快穿反派是我老婆bylu123 > 第95章(第1页)
第95章(第1页)
孙悦白抚着额头,无奈的摇头,这人依旧还是那个性格顽劣张扬的青年,哪里还有刚刚言之凿凿,进退有度的模样。
这一刻,讲堂是属于安殊亭的,没有人注意到万安和脸色有多么难看,一种深深的无力让他扑通一声跌坐在椅子上。
这样大气的格局思维自己有吗?
从前教过他的先生都说他在读书一道有天分,万安和素来骄矜自傲。
便是出身农家,底子薄弱,自入书院以后,他也逐渐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可自从遇上安殊亭便屡屡受挫,寒窗数十载,竟比不得一个刚入学堂的纨绔。
又或者是来自于知州大人家的耳濡目染,万安和有些失神的看着讲堂里的众人。
“安和兄?”
蓝善佑看着万安和怔然失神,一蹶不振的模样,眼带急色,低声喊了万安和一声。
万安和的耳朵里此刻听不见任何声音,他的望着讲堂正前方的天道酬勤几个字。
见万安和没有反应,他抬手摇了摇万安和的肩膀。
“这会儿发什么呆?你从前可不是轻易放弃的人,安殊亭不过是一时占了上风,咱们还有机会不是吗?先生如今向着安殊亭,所以你连孟大人也要放弃了吗?”
蓝善佑实在不解,从前他们也不是没有遇到过挫折,这次竟对万安和打击这般大。
可再不理解,他也要警醒万安和,这次机会对他们这种没有家世的农家学子有多重要,万安和这些日子跑前跑后私下里又做了多少,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更遑论他们几个人也付出了那么多心力,就是为了推万安和一把,除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未必不是存着为自己铺设人脉的心思。
明明马上就要成功了,偏偏插进来一个安殊亭。
还有先生,万安和听见先生总算回过神来,就看见素来淡雅温和的先生满目专注的看着安殊亭。
包容、赞善、带着细碎的微光,那还是目下无尘,矜贵傲然的先生吗?皎皎明月就该高高的挂在天上,但凡沾染了烟火,就仿佛被污染了一般。
万安和不再去看那边,垂在身侧的指尖似乎颤抖了一下,一时间心头浮现许多,“我知道,你放心”
。
蓝善佑总算松了一口气,微微眯眼,略带讽刺的说道,“你相信一个连论语都写得错误百出得纨绔子弟,能做出这样的论述。”
他就要站起来,却被万安和一把按住,“他并非你我印象中的草包,不要冲动”
。
蓝善佑一把挥开万安和的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遇上安殊亭就畏手畏脚,难道他这两次的侥幸得胜将你打成了一个懦夫吗?”
他眯着眼睛看着安殊亭和孟大人侃侃而谈的模样,说话语气颇为不忿。
万安和知道蓝善佑是同自己之前一般钻了牛角尖儿。
“谁又能靠侥幸屡屡得胜,孟大人这时候正对安殊亭赞赏有加,贸贸然挑起冲突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万安和语气深沉,前些日子安殊亭的警告还历历在目,只那一个照面,万安和便知道这是个有心计手段的,绝非善类。
蓝善佑闻言满脸的不服气,“就算他这两次表现的十分出色,你又能保证这就是他的真才实学。”
“凭着安家和先生,就算是找人捉刀也不是不可能,不是吗?他那样的课业水平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有如此精妙绝伦的论辩。”
安殊亭的消息大部分是蓝善佑打听到的,他对自己调查到的东西深信不疑,或者说他打心眼里不愿意相信有人的只凭一句轻飘飘的天分就可以打败别人数十年寒窗苦读。
万安和拉着蓝善佑的手有些松动,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人为操控的。
就比如说他这些日子主动跑去山长那里帮忙,时时侍奉左右,知道他二人近日极为关注北方旱灾,只一提到百姓颗粒无收就忧愁不已。
万安和回去后便默默的整理了许多关于赈灾、农业等方面的东西,这才有了今天的一鸣惊人。
这算不上作弊,但令他比其他同窗多了几分先机。
见万安和不再说话,蓝善佑深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桌上的纸,顺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又暗暗打量了一眼孙悦白,咬牙。
“我有疑问。”
讲堂这会儿满是细细得讨论声,一时间没有人注意到蓝善佑,他将手里的纸张高高举起,放开了嗓音,“我有不解之处望能得解惑。”
这下子众人的视线终于注意到蓝善佑了。
安殊亭停下了和孟大人的交谈,似笑非笑的目光直直射向蓝善佑。
蓝善佑心头一跳,随即反应过来安殊亭不过一个草包,自己如何会被他的目光刺到,很快又挺起胸膛。
“我听你提起当今的革新之策,从前朝到现在的土地制度皆是言之凿凿,那么历朝历代多次实行土地变法之道的根源是什么呢?”
安殊亭收敛了脸上的笑意,指尖无意识的在桌面打圈,这个问题的答案早有前人谈起,蓝善佑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在这个时候问出来,总不能只是毫无意义的普通互动。
安殊亭目光深沉的看向与蓝善佑坐在一处的万安和,所以他们这是怀疑自己作弊?安殊亭抿唇对上孙悦白略带深思的目光,看着那二人面若寒霜,怕是连孙悦白的风评也被自己带累了。
这个万安和吃了几次亏难道是个傻子吗?抑或是原主不学无术的形象太深入人心。
“才华横溢的知州家公子,怎么连这样简单的问题还要思考这么久。”
见安殊亭沉吟不语,蓝善佑忍不住质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