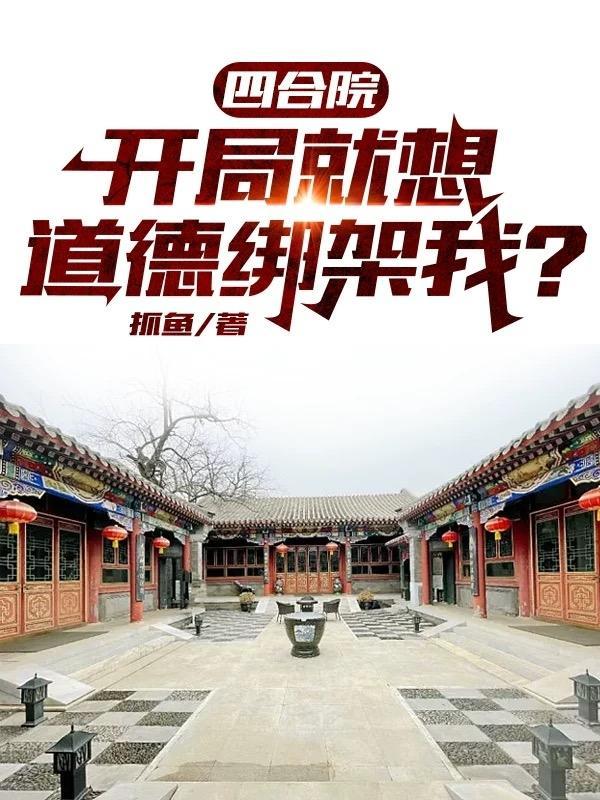69书吧>被敌国将军当成白月光后笔趣阁 > 第34章(第2页)
第34章(第2页)
她乃是大唐公主,金枝玉叶,如今竟要像乐馆伶人一般为胡人作舞取悦,实乃大耻。
见她不语,他语气又重了些,说道:
“回鹘,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辰霜撅起了嘴,不想与他辩驳,只瞥了他一眼,惊声道:
“哎,你脸上的伤哪来的?”
司徒陵见状,云淡风轻道,“没什么。刀剑无眼,常有的事。”
辰霜在心里嗤了一声,方才明明没有的,血迹都没干,定是一刻前才新添的。
见他不断描绘着明日之行有多险,她反而觉得不过尔尔,心中无甚感觉。
是了。再险、再痛,可与五年前失去那个少年的感受相比吗?
不能,再也不能了。所以她的心,其实早就空荡荡了。
被掳到回鹘,受过鞭刑,箭伤不愈,手掌被匕首割破数道伤口,身体受过各种各样的罪,好像也唤不起心底的一丝情绪。她的心,每一年,都越发的迟钝而滞重了。
辰霜不想再听他劝,便扯开话题,故作不经意地问道:
“你来回鹘四年,可是见过长姐了?”
“见过。”
他干脆答完之后,久久不再做声。
“你们……”
辰霜按捺住心底的疑问,话到嘴边,却始终问不出口。
“年少无知,往事已矣,不必再提。”
他转身面向辰霜,眸色暗淡,面无表情地问道,“我若是此时再问你长风的事,你又会如何作答?”
易地而处,确实是有苦难言,辰霜便将话咽了下去,不再开口。
塞外茫茫,夜风惶惶,吹皱了二人各自沉于心底的陈年旧事。明明已是三缄其口,却又忍不住涌上心头。
“你睡吧,哥守着你。明日还有场硬仗要打呢。”
他踩灭了几处被风吹起乱跳的星火,又帮她紧了紧大氅。
辰霜已随大军疾行了一日一夜,此刻力气耗尽,眼皮也越来越重,只觉面前的火光越来越暗,不一会儿便抱胸趴在膝上睡去了。
云升云起,倏忽间掩住了月色,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掌,搂住了下坠的玉盘。
已是夜半之时,朔风呜咽如泣,不知何处传来的夜鸣声将睡梦中的辰霜惊醒。
她警觉地睁开眼,只看见湮灭的篝火已化为青烟袅袅,周遭只有玄军守夜的巡逻兵规律地脚步声。
只是虚惊一场。
十多年来,她在军中养成习惯,向来睡得极浅,从不敢深眠。醒了,便再也难以入睡。
她的意识和身体浑然都苏醒过了,这会儿只觉得喉咙干涩。大漠中行军,水本是紧缺的,一路上她脸皮薄,也没问身旁的几个骑兵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