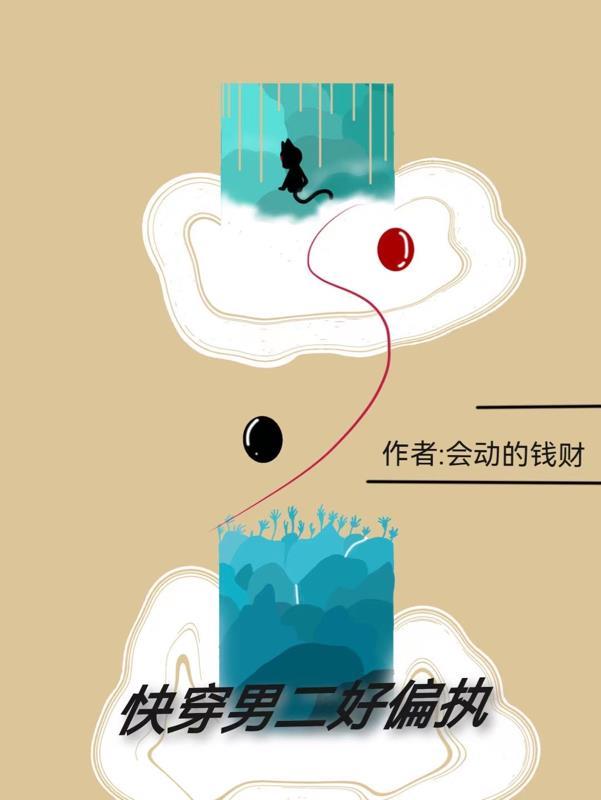69书吧>替身编号005by > 第43章(第1页)
第43章(第1页)
联最后望了一会儿儿子的归处,转身离开。
伦道夫望着他的背影:“阁下。”
联暂时停住脚步,转过身。
“任何事都不会让我停止为您感到骄傲。”
阳光垂落,苍白的丛泛着金色的光泽。联静默片刻,转身离去。
走到墓园边上,他看到了伫立在树荫下的钟长诀。
对方冲他敬礼。他转身走入林中,钟长诀随即跟上了。
墓园背山靠水,景色极佳,后方便是浓密的阔叶林。两人的脚步沙沙响着,钟长诀很好奇,走到哪里,对方会掏出枪来,指向自己。
可始终没有。
就像之前每一次在蓝港树林中的密谈一样,联只是问他军备情况,战略部署。
就好像弗里曼的死从未生,就好像之前用枪顶着他的暴怒父亲从未存在。
钟长诀观察他的脸,白比往常多了,皱纹也愈加深陷,可除此之外,没有怒火,没有嫉恨,只有严肃和沉思。
这让钟长诀感到心惊。
在讨论间隙,钟长诀提出殉国将士的话题,联看了他一眼:“你想问什么,直说吧。”
他答得如此坦然,钟长诀明白,事情已有定论:“上尉的事,您就这么过去了?”
联的语气带着些嘲讽:“怎么,你觉得我会毙了你?”
钟长诀不答。
“这是不可能的事,”
联说,“对国家来说,你比一百个弗里曼·贝肯还要重要,他哪里值得拉你陪葬?”
联就这样轻轻放下,他反而更加恐惧。
联拍拍他的肩:“人民需要你,至于我个人的好恶,那实在是次要的事。”
钟长诀深吸一口气。唯一的儿子死去,这人在短暂的暴怒后,竟然能迅冷静,评估形式,压下所有情绪,选择最好的处理方式。
儿子已经死了,报复也救不回来,那干脆把他变成政治资本。
又或者,联说的是实话?
在他的政坛之路上,钟长诀远比儿子重要,他完全可以放弃一个来保住另一个。
突然,钟长诀脑中涌出一个场景,一个猜想。这猜想太阴暗,刚出现时,他甚至感到荒谬。
然而,如同坠入水中的墨汁,它迅蔓延,侵占了神智的各个角落。
在他原本的计划中,弗里曼中毒后,器官会大幅受损,只能躺在床上过完后半生——痛苦至极,但不会死。毕竟他能获得最好的医疗资源。
钟长诀并不想让他死,他是霍尔案的人证,是夏厅的漏洞,最好挺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治疗的前几天,弗里曼并没有生命危险,为什么情况急转直下了呢?
当然,霖毒有时会造成医学影像无法观测的损害,也许就是延迟作了,但是……
钟长诀眼前闪过一个场景。
白老人站在床前,凝视着病床上的儿子。注定残疾的、沉溺于痛苦中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