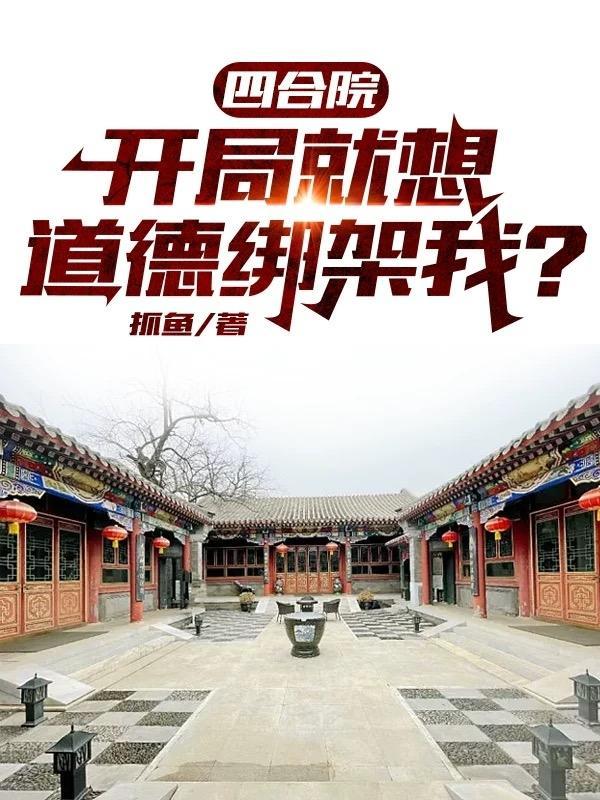69书吧>戏连城原著在哪看 > 第六十七章(第1页)
第六十七章(第1页)
雪停了,天空中朦胧的太阳,似带着几分睡意,过了头顶向西边斜去,瞧着意思孙庆三是找不着了。
马彪腹中无食,浑身没劲,腿一软,一屁股就坐在马路牙子上,再也不想动弹了。
一辆轿车飞驰而过,雪后的马路上泥泞多水,汽车溅起的泥水,飞溅了马彪一身,这会儿了,亲朋无一人,人穷狗都欺。
轿车后座上的女人看不过去了,虽然是个路倒,咱也不能怎么糟贱人家,她让司机停下车,女人下了车,转回身,来到垂头丧气,坐在马路沿的马彪身边,她让司机将马彪扶起身:‘’对不住您啦,溅了您这一身泥水,怎么着吧,您把这外罩脱了,我给您送洗,再给您找个干净的澡堂子,浣洗浣洗?‘’
二人连推在架,将马彪送到涌泉堂门口,司机脱去马彪的大衣,女人现,这位里面穿的竟是套毛哔叽西装,瞧这主儿的打扮,不像个叫花子呀?女人翻了翻马彪的大衣口袋,里面有个名片夹,女人抽出一张名片瞧了眼,北平市政务委员‘’千里沙‘’这是个人物啊?‘’千先生,您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
马彪瞧了眼女人,耷拉下脑袋:‘’夫人,我这是让人家给坑啦,让人抢了。‘’
女人点点头:‘’我瞧出来了,怎么着您去洗个澡,收拾收拾,以后您有什么难处,您上这地儿找我。‘’说着递给马彪张名片。
马彪抬头瞧了瞧涌泉堂的大门,迈不动步了,为难地说道:‘’夫人不瞒您说,我这兜里,镚子没有啊。‘’
女人微笑道:‘’您这是落难了,我瞧出来了,她从提包里掏出3块大洋,得您先用着,回头再说。‘’女人上车走了。
进了澡堂子门,饿狼似的马彪,就赶紧让伙计叫两份包子,一碗热汤面,送进来,马彪又沏了壶茶叶沫子,坐在小木床上,吃得舒舒服服,吃饱喝足了,马彪又在涌泉堂里,足足泡了一个下午,舒坦!
到天擦黑,马彪才从浴池出来,大衣熨烫的干净,皮鞋擦得净亮,肚里热,身上暖,马彪回头瞧了瞧澡堂子门框上的对子‘’金鸡未叫汤先热,红日初升客满堂‘’嘿嘿…我马彪两天的工夫,换了两活法。
马彪双手向大衣口袋里一插,摸到了女人给他留下的那张名片,掏出来瞧了瞧‘’金芙蓉‘’这女人,可真是位女菩萨,洗澡、洗衣裳,吃了顿饭,花去人家一块大洋,这兜里还剩下两块钱,虽然刚才在澡堂子里鞦了一觉,这黑灯瞎火地往哪去呀?他一琢磨,转过身儿,又进了澡堂子:‘’掌柜的再住一宿。‘’
住澡堂子古来有之,白天洗澡,晚上清静了,有那花5毛一块的主儿,图便宜,跟澡堂子忍一宿,马彪算了账,兜里这两块大洋我要是去住店,就管不了肚子,唯独住澡堂子,是又管我睡,又能管我吃的地界儿。
掌柜的瞧这位先生穿戴怎么立正,住澡堂子?八成这是遇到难处了吧?‘’得这位爷,让您受委屈,怎么着,我给您安排个单间盆堂的位置,你踏踏实实地跟着歇着。‘’
躺在床板上的马彪,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这宿是有地忍了,明可咋办,还歹到大街上溜达去?他摸出大衣口袋里的名片,都掏出来查看了一遍,把那夫人的名片,单独挑出来,又把自己的名片,一股脑泡了水,揉成团,扔在纸篓里,别它妈丢人现眼啦。
看看金芙蓉的名片上有电话有住址,稀罕!昨个马彪就瞧出来了,跟北平城里,能坐着外国汽车满大街跑的女人,绝非凡人。
这下一步该奔哪啊?我从那能做点什么,挣出笔路费钱,去汉口找白凤凰啊?
潘月桂这孙子,害得我好苦啊!马彪突然想起方和安想杀潘月桂那档事,哎…这倒是条出路,去跟方和安那讲条件,如果我马彪杀了潘月桂,他方和安不会不帮我。有了这主意,马彪心里头踏实多了,他决定明天去北平行辕署,去见方和安。
三月,一场雪后,北平城的天气开启了小阳春,暖暖的春意,尽洒在这座古城的天空大地。没几天的工夫,城里城外路边,野地已是一片翠绿。
天气暖和,太阳挂在蓝天上的日子,也渐渐地长起来,蛰伏一冬的人们,脱去厚厚的棉衣,暖靴,换上了薄衣马褂,脚蹬套鞋,便鞋,千层底。街上的人们步履轻盈,浑身上下,透着那么轻松舒服,脸上洋溢着暖日,春香的愉悦。
春天,总是让人们充满希望,一年使于春,它是催促人们向上奋起的季节。
春暖花开的时节,阳气,升浊气降,日长,月短,天儿不凉不热,这是戏班子最好的演出时光,戏园子里没有冬季的寒冷,夏天的燥热。春天清爽透气,这日子听戏,两字“舒坦”
。
泰和戏园子这些日子,隔天戏票,头天就卖个精光,瞧戏的客人,场场爆满。
可蔺兰庭高兴不起来,这些天,每逢开戏时,他都是愁眉苦脸,一人儿坐在后台里唉声叹气。乌泱泱的人群,往鲜鱼口里头涌,都奔的是咱这泰和戏班子,这情景,它不在常理儿上啊?蔺兰庭总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就要临头似的?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自从舞燕的安天会唱红,应了那句话:人红是非多!
这些日子,北平报界的记者,也是闻风而动,几位报社记者,天天泡在戏园子里,报道这位红透了半个北平城的女猴王。
各种报纸,争相刊登各色美文,写得尽是些赞美之词,又配上一些戏装照片,那年代报纸捧角儿,那可是天降的厚爱。
记者们在采访舞燕,舞蝶时,又给两姑娘拍摄了大量生活照,一并刊登在报纸上。
舞燕舞蝶的生活照,在北平城里的公子,少爷圈里,引起了轩然大波:用‘’十七妙龄,美艳绝伦,绝代双娇,倾献绝艺‘’来赞美这两位刚满十七八岁的名家新秀,再配上舞台上的戏照,这对光彩照人的彩花旦,这工夫用啥溢美之辞,都不为过。
没过多少日子,泰和戏园子戏场子,成了北平名流公子,少爷们的专场。这帮公子王孙,如同屎克螂嗅粪蛋子,小蜜蜂逐花香一般,从京城各个角落,汇集到了鲜鱼口。
花红招浪蝶,酒香招云客。每逢演出时,戏园子里外,是乌烟瘴气,还有那几位为争风吃醋,而聚在一起打架斗殴的主,这些日子,泰和戏园子,可真成了前门外头的一景。
戏还没开锣,金崇琛去外面戏票房那看了看,戏园子门前人群已经是乌泱乌泱,他不放心,进戏园子又从前面客座绕了一圈,就现不妙,有几位少爷又是抬着花篮来的。
那年月,那时节,整些个鲜花绿草,不容易,能弄出这等风雅玩意的,可都不是等闲之辈,您瞅个顶个的拿谱,个顶个的有做派。
来人里面有一位少爷,气势压人,这位二十四五的年纪,身量有5尺多高,足有二百多斤的黑胖子,听说:是北平城公安局,廖副局长的公子,廖书衡。这主逢场必到,早早就来园子候着场,回回来,身旁的跟随,抬着个大花篮。
这位戏德不赖,不闹腾,不嚷嚷,也不去抢那官座,开戏时,在最前排寻个散坐,桌前面一坐,不吵不闹,心无旁骛,两只眼直勾勾盯着戏台,瞧意思,他那份心思,全在戏台子上那搁着。
昨儿个巜樊江关》刚唱完,舞燕跟舞蝶说:‘’您瞧见了吧,又来了,这主儿瞧戏,瞧得我呀,见他都瘆人的慌,两眼珠子不措珠,死盯着不离您的身儿,像是要一口,把人吞下去的模样。‘’
‘’嗯…瞧见了,那眼神,狠呆呆的,跟黑熊瞎子似的,怪吓唬人的。‘’舞蝶也是没好气地说道。
廖书衡凡是舞燕的戏,一场不落,只等舞燕谢幕完毕,落下花篮,抬屁股就走,头也不回,这位是闹的什么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