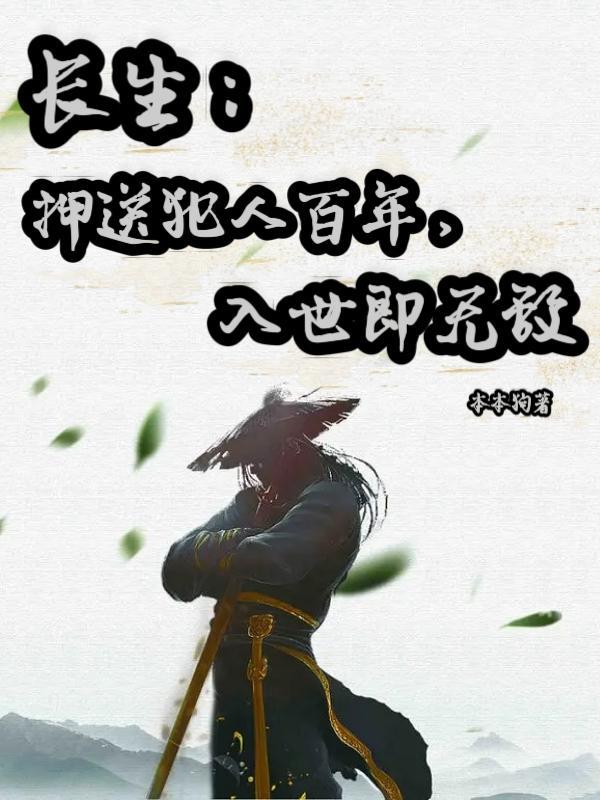69书吧>与君分杯水 千里孤陵 > 第64章(第1页)
第64章(第1页)
“我不要看一堆堆侍女。我不要看一堆堆大伯和老头……”
六嫂抓狂。“我要看帅帅的美美的王爷、待卫、军士、臣子、太医、书僮、花匠、菜农、百姓、戏子、艺人,我要看奸情啊呜呜呜……”
大理寺寺丞谢匡把下人早早打发下去,独自在书房里踱了两圈坐下来,静听着远处更鼓悠悠的传来。
想必石阶被雨雾打湿,一行脚步踏在上头,低沉得若有若无。小厮来在门外,敲了敲门,悄悄的叫一声:“大人。”
谢匡忙道:“快请。”
门一开,一股寒气就侵了进来。借着房内一盏蜡台,依稀可见黑夜里如丝纷飞的雨雾。来的只是独自一人,裹在一袭石青色的刻丝貂领披风内,并不作声。在门外沉静的站了片刻,这才提着袍角缓缓跨进门来。小厮在身后低眉顺眼的将门关上,悄悄的退下去。
谢匡看清来人,却微微有些吃惊,仍不敢怠慢,把人迎到座上。亲自去一旁红泥火泥上取水沏茶。
“大人不必客气。”
来人把风帽拉下来,露出一张苍白的脸,一边淡淡的说。
“是。”
谢匡答道,倒了两杯茶。沉默了一阵,这才慢慢又说:“下官记得,下官今日邀请的,并不是九王爷您。”
“六哥今日插不出身来。何况有些话,大人直接问我大约更方便些。”
容瑄微微颔首,垂下眼去注目手中的杯子。
谢匡还是先帝时任命的大理寺丞,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十余载。为人冷静灵敏不偏不依,看人的眼光凌厉老道。是以他压着平章殿宫人一事,不容外人插手,濮王爷一时竟也奈何他不得。
此时听容瑄这么一说,抬眼略略扫了一眼。平平道:“是。”
然而来的人是他,有些话说起来并非方便,而实在是不便。然而看九王爷似乎执意上门过问此事,一时沉吟不决。
容瑄怕冷似的捧着杯子,却又不说话了。
“下官身任大理寺丞,身份驳正之责,有些事就容不得私情,也顾不得情面。有得罪之处,还请王爷体谅。”
谢匡朝容瑄恭恭敬敬施了一礼,说话间却毫不拖泥带水。“请问王爷可认识太章殿洒扫太监福清?有无私怨?”
谢匡看着对面那人神色慢慢僵硬,却没有多少表情。半晌才道:“从未见过,也没有私怨。”
“福清在宫中不聚赌,不好财。向来默默无闻,行事从不张扬。同殿的内监都没有几个同他相熟的。想必王爷也是不认识。这人无父无母,再无亲戚可查访。他的衣物用品中也非搜出银两钱物。说这人一时动了贪念,委实不通。且此人貌似不堪,然而言词间条理清楚。一番刑讯下来,竟从未有过胡乱改口之词。如此之人,明知那玉是皇上身上之物……”
谢匡但稍一想,还是忍住口。将一应案宗及忤作检尸的结果放到桌上。只道“怎么轻易做出这样引火上身的事。若同王爷并无私怨,委实耐人寻味得很。”
宫中之人,明哲保身的道理皆有不懂,若真是撞破如此内情,只有恨爹妈多生了眼睛耳朵,那里还敢打这玉的主意,何况此人从未有受财一说,又没有什么急等要用钱的地方。这意思,他不说,容瑄自然也领会得。然而此事提及,却委实难堪。
更住深里说,这人若是有人布下的眼线棋子,当真可算得上神不知鬼不觉。但这般用法,却似乎急迫了些。
容瑄嗯了一声,略略翻了一翻,坐在那里就微微有些出神。
“王爷。”
谢匡咳了一声。“去年五月初六,皇上大婚当日,王爷可曾宿在宫中?”
容瑄抬起头来,见大理寺丞向来沉静的脸上,微微露出一丝怜悯的意思。正默默的看着他。见他神色漠漠,仿佛听若未闻。轻声道:“福清自然是污隐王爷。但那日的时辰,宫中往来的人物,就连侍卫间如何换防,平章殿所有人手何时调开,都能说得分毫不差。就算他没有亲见,总也得有人教唆着他。”
容瑄茫然看着他,似是不能明白他所听到的。只是想,有人看到么,那夜的事,真的有人看到么?这么一想,半个身子几乎都冷了。
“恕下官无理。但下官职责所在,有些话不得不问。”
耳边听得谢匡的声音还在说。“皇上……”
“放肆。这同皇上有什么关系?”
容瑄猛然醒了,断然喝止。“大人好大的胆子,也要学那些乱臣贼子,诋毁皇止清誉么?”
“下官不敢。臣负大理寺卿职责,事有冤枉者,推情详明,务必刑归有罪,不陷无辜。这是王爷私事,然而事关重大,就算臣今日不问,日后总有人背后猜测。平空多生事端。”
谢匡见他动怒,一起身就在他面前地上跪了,却仍看着他。“花红一事,并非平地生风。”
“那也是我的事,同皇上没有分毫关系。大人起来吧。”
容瑄看着他,神色反而冷淡平静起来,伸手来扶,“谢大人也是为官多年,大人的行事为人自然清正,做事但求水落石出。但这等有损圣上英德的话,日后再不要提。”
“王爷今日就不该来,别的事还是改日再谈的好。”
谢匡看他形容萧索倦怠,显然无意多言,意思却果决,无端生出分凉意。微微叹口气,果真起身不提此事。
“总得亲自来看看。”
容瑄静了一会,方才低声道。“这些卷宗,我就代谢大人回禀。”
谢匡应是,料想这些卷宗,却必然是到不了天子手中,不由得皱起眉来。默默看他收拾起桌上案宗,手指却微微有些发颤。过去帮他收拾,被容瑄一手压住,低声道:“我自己来。”
慢慢的将厚厚一送纸张放进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