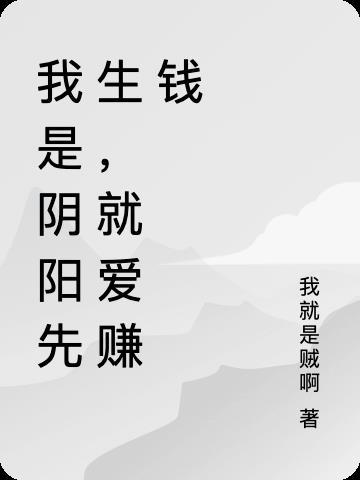69书吧>史上最强大反派 > 第60章(第1页)
第60章(第1页)
>
紧接着,黑影点燃火折子直接走了进去,在微弱的光照下,一条狭窄的甬道展现在眼前。他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后,进了一间宽敞的石室,他用手中的火折子点燃了角落的两支火把,举目望去,这间石室布局简单,除角落的床榻和正中的书案外,别无他物。
书案上摆放着几个木盒,黑影走过将木盒重新摆放好后,并按照特定顺序逐个轻击,三次过后,床榻上忽然发出“啪”
的一声,随之又呈现两个木盒。
黑影缓缓走近,轻启其中一个木盒,内里竟然藏有一半虎符。顿时,黑影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同时抹去额头上的汗水……
突然,“扑”
的一声轻响,火把瞬间熄灭,石屋内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
黑影警觉地伸手摸向身后的弯刀,准备应对潜在威胁。然而,又是一声“扑”
的轻响,火把竟然自行重新点燃,石屋再次明亮起来。
然而,黑影发现屋内多了两个人,正冷冷地盯着他。
“刺史大人,见到本相还不行礼?”
温之言眸色深沉,语调清厉。
此刻,床榻之上,手持木盒的竟然是洛州刺史淳于简,他右手隐于腰后,似乎在寻求脱身之计。
温之言身侧的裴伦逼近一步,警告道:“刺史大人,我劝你还是别存侥幸心理,尽早交代对你我都好。”
淳于简凝视温之言许久,方才发问:“你们是如何发现的?”
温之言居高临下地看着淳于简,缓缓说道:“我一直很好奇,洛州水渠堵塞案中,你和徐山其实没有必要对司仓参军下毒手。毕竟,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一旦船沉,无人能逃。因此,比起杀了他,利用他的供词将责任推给尚书令岂不更为明智?而你,也确实是这么做了,只不过却是在你杀了司仓参军之后……”
淳于简面色苍白,因为,站在他对面的人,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保持着从容不迫、威严自若的态度。
“因此,我推测,你杀害司仓参军并非仅仅因为水渠事件,而是因为他掌握了你的某些秘密。后来,我偶然得知南海剑派与洛州官员有往来,于是猜想你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真正身份被曝光。”
温之言伸手向后探去,取出了那幅他曾与裴伦共同审阅的画轴。在展开画轴后,他继续阐述:“司仓参军乃进士出身,通晓六艺,因此他将你所隐瞒的秘密,巧妙地寓于这幅画作之中。”
裴伦听闻此言,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温之言则微笑着,仿佛洞察了他的内心所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最初,我也误以为它仅是描绘一段隐晦的男女情感的画。”
温之言左手持画轴,右手在其上滑过,继续解释道:“然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画中的初旭之光仅洒落在西山之巅,与高楼相映。这寓意着只有西山能够永远沐浴在日出的光辉之中。将‘永’与‘日’二字结合,便形成了‘昶’字。而所有飘浮的云层全都半遮半掩于虎头之上,若将‘全’字去掉上半部分,剩下的便是‘王’字……”
温之言犀利地指出,“所有线索合在一起,便是“昶王谋反,刺史募兵。”
裴伦瞪大了眼睛,惊愕之情溢于言表:“昶王,先皇的第六子,竟然谋反?这怎么可能!”
淳于简此时神色苍白,颇感困惑,询问道:“温相的眼光果然独到,从画中竟能看出这么多,真是令人佩服。但我不明白,你为何知道我今晚会来这里?”
温之言将画卷递与裴伦,坦言道:“我在洞悉这幅画作之谜后,便刻意让你知晓我曾致信昶王,他之所以留你一命,定是因为你手中掌握了他所需之物。因此,当你看到那封专为你所写的信时,必定惊慌不已。而我,只需静待你自行暴露破绽即可。”
淳于简深深叹息,眼中一片死寂,仿佛在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既然天意如此,我也无话可说……”
温之言双掌交握于腹部,身形笔直,透露出不容忽视的王者气概。“既然都是死,你有两个选择:一是随我赴京,将你的事如实陈述,以求速死;二是我将你交给南海剑派的人处置,看看究竟是挑断筋脉更为痛苦,还是服下种种剧毒更为痛苦……”
淳于简惊恐地摇首,“不,不,你不能把我交给南海剑派!我可以随你进京,但你必须确保我的家人不受伤害。”
温之言轻蔑地冷笑一声,“你所犯下的罪行,十个脑袋都不够砍!还妄想家人不受牵连?真是痴心妄想!”
淳于简此刻犹如一头濒死的狼,见人就咬,“那又如何?若你想救温韶,就必须保障我家人的安全!否则,即便我死,也不会随你进京!”
在温之言为温韶洗冤之际,叶槿容亦在京中积极奔走,她于清宁苑飞月阁亭台中,向叶景渊郑重质询:“皇兄,温韶身为两朝元老,政绩卓着,门生遍布。如此仓促定案,不怕寒了朝中老臣的心吗?”
叶景渊直视她,沉声道:“此案不能再继续往下查,始于温韶就只能终于温韶,否则,若再深究下去,恐怕连定北侯也会被卷入其中。”
“定北侯与本案有何关系?他只是温韶的侄女婿,并且三年来一直在西北边境。”
叶槿容质疑道。
叶景渊将手中紧握的文书递给她,面色凝重地说:“近日,各地刺史纷纷上奏弹劾温韶,且这些奏报全都绕过了御史台,直接由梁仁辅呈递给朕。最严重的是,冀州江阴侯与韩太尉亦同时上书,要求朕必须严惩温韶。此外,西北边境传来紧急军报,称定北侯的小股军队出现在石泉关、万重山、五阙岭等地。朕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若被梁仁辅抓住把柄借题发挥,那西北兵权恐有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