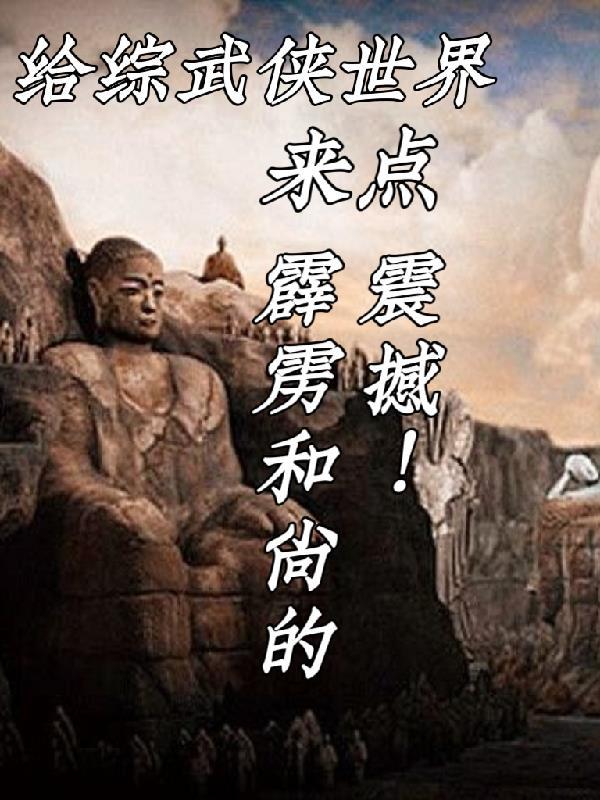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种子方舟演讲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吴守愚的食指都屈好了伸出来,最后只能敲敲自己的脑袋,负手走开。
“这孩子学医,难道是入错了行?”
三天后,吴守愚把余歌叫来:“永言,你去一趟柏县,找到百草堂的徐师傅,把我半年前订下的药取回来。”
“还去呀?”
余歌道,“为了您这药,我都去两回了,次次扑个空,我看这次也是一样。”
“徐师傅是诚信人,他说给我带回来,肯定能带到,”
吴守愚道,“现在世道不同了,边境多事,西夷占着上风,关外的药材,难运进关内,有人千辛万苦才带回来一些,要么是被抢光了,要么是留下自用舍不得给人,我想求一些,只能托徐师傅。你别嫌麻烦,再去一回。半年都过了,徐师傅一定回来了。”
余歌只好答应着上路。走了半月,到了柏县,熟门熟路,找到百草堂,里面又挤得都是人,余歌好不容易拉住一个伙计,问“徐师傅回来了吗?”
“你说徐师傅?他是从关外回来了,但是现在不在,出去了,要不你等会儿吧。”
伙计答道。
余歌无法,只得出了百草堂,见那路边上一棵柏树,有人在那下面坐着歇脚,便走了过去,将马拴上去。本想进马车睡觉,可是嫌闷得慌,这外面倒还有点儿风,柏树下面坐着也凉快,余歌便和那两三个歇脚的人一样,坐下来,靠上树干,打开扇子对着脸摇。
没过多久,脸上的汗干了,连着赶路的余歌便犯起困来,后脑勺抵着树竟睡着了。他睡着期间,太阳逐渐偏西,旁边歇脚的人也起身走了,马拖着车绕到另一边去,有个青年路过,扭头往这看了一眼,竟愣住了。
这时的余歌,沐浴在夕阳的晚照之中,几丝乱发在风里飘动,一腿伸直了在地下,另一腿屈起,手里握着折扇,松松地搭在那只腿的膝盖上;头背都靠着树,光洁饱满的额头和似在轻笑的唇角,显得他安适恬淡,虽是睡着了,却比那些利来利往的熙熙攘攘都要灵动鲜活。
青年觉得,自己定是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幅画儿。这一幕难道不是像画一样吗?只恨自己不会丹青,不能描绘下来,日日看着回味。
从百草堂里跑出一个小伙计,出门到处望了望,看到柏树下的余歌,又向这跑来。
“起来,起来,”
他摇着余歌道,“你不是要找徐师傅吗?他回来了,你倒是起来啊!”
余歌被摇醒,听到他的话,一下子蹦起来:“在哪呢?”
看着余歌匆匆忙忙随伙计去了,那个方才看了他许久的青年怅然若失,叹了口气,再望一望,最终走了。
“徐师傅!徐师傅,我可见着您真容啦!”
余歌一面追赶着快步前行的徐春,一边说,“我师父派我来拿药呢!这都是第三次啦!”
“哦,永言啊,”
徐春看了他一眼,“你恐怕还得再等会儿,我这要去房里,搁了东西,再换身衣裳,还要赶在太阳落山前,去炮制房教他们炒王不留行籽……你都等了这么久了,不在乎多等会儿,是吧?”
“可是,徐师傅……”
余歌可不愿意等,听徐春这么说,只得蔫了气站住。
徐春走回房间,才发现余歌没再跟着他了,不知道哪儿去了。他还有一堆事,便暂且没理会,赶紧放下东西,换了一身衣服,出了门往炮制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