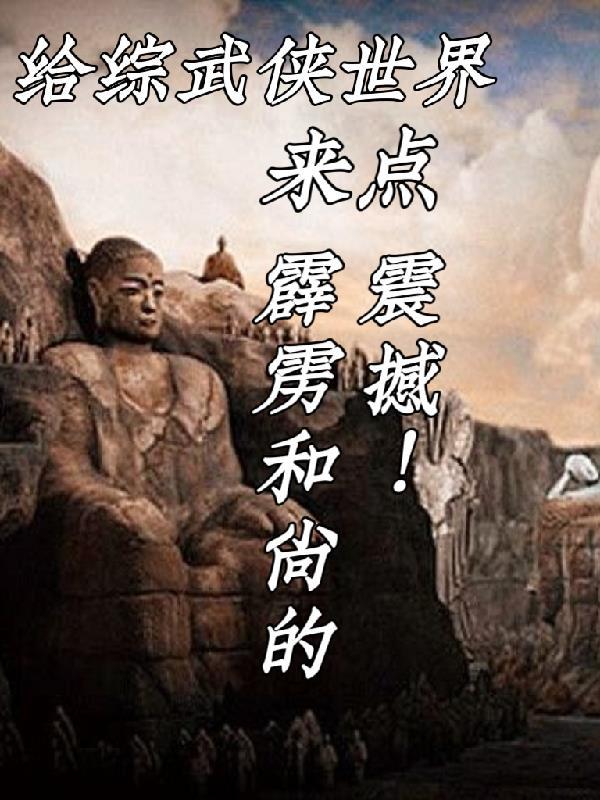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天地无私玉万家和立冬有关吗 > 第49页(第1页)
第49页(第1页)
郑半山不太习惯这样的杨楝,不免有些恼怒,便道:“这雀儿生病了,你知道不?”
“知道,程宁派来送书的人和我提过。”
杨楝道,“说她偶感风寒,我叫他们好生照料着,想来已经病愈——先生如何得知,去看过她吗?”
“我是想去看看,却被你的人拦下了。”
郑半山道。
觉出其中有异,杨楝吃了一惊。
“我还是听坤宁宫的曹典籍说起的。”
郑半山冷冷道,“因皇后赏赐下一些东西,琴小姐却称病不能谢恩,所以几位女官领了懿旨前去探病。据曹典籍讲,琴小姐自那晚之后便一病不起,情形很是不妙。”
总不会是因为……杨楝想起琴太微满面泪痕的模样,一时怔忡,咬着嘴唇说不出话。
“我听说此事,想去看看,你的管家娘子却说琴小姐病已见好,而且内宅姬妾不宜见人——如此我也无法了。”
郑半山道,“这还是月初的事,如今竟不知如何了。”
“是陈烟萝?”
杨楝思索道。
“不是她还有谁?”
郑半山还想再催促杨楝几句,却见他面色僵冷,只是低头向前走去,一个字也不想再说。
正午的日光穿过林杪,斑斑驳驳地落在杨楝身上,随着衣袂摆动而闪烁不定,如这少年琢磨不透的心思。郑半山心中再次泛起隐忧。当时他听说杨楝纳了琴太微,只觉匪夷所思。琴灵宪的事情始终是杨楝的心病。如今琴太微到了他跟前,只怕这心病更不能消解,只会愈演愈烈。但他除了观望,又能若何?
徵王府众人只知杨楝回府的日子是六月十三。可是六月十一,杨楝忽然出现在清馥殿廊檐下,上上下下都被闹了个措手不及。杨楝将众人扫视一圈,现琴太微不曾列于其中,心知自己这回马枪多半是杀对了。等程宁回了几句话,他便先问起琴太微的状况来。陈烟萝遂引了他去后院探看病人。清馥殿仅有两进院落,杨楝自己住了前院。因王妃位虚,后院的正房便一直空着,几位侧室各分一间厢房居住。
琴太微被安置在东边一间阴暗的耳房里。杨楝一见,先自皱起了眉头。陈烟萝见状,只得道:“本来是让她和林夫人一起住在东厢的。只是她病得太久,怕给旁人过了病气,所以暂时挪到这里来了。”
杨楝也不说什么,撩开帐子,见琴太微埋在一堆揉皱的被褥之间,轻薄淡白有如一缕幽魂,唯有两颧染着奇异的红色。她听见有人来,抬起眼皮茫然地瞧着。似乎过了一会儿,她才想起来他是谁,忽然一咬嘴唇侧过脸去。杨楝放下帐子,默了一会儿,扭头看见医婆6氏正跪在旁边,便索了药方来查看。
只是些寻常方剂,虽不算高明也无甚大错,对付小小一桩风寒也尽够了,怎会拖成病入膏肓?6氏战战兢兢地垂了头,只说琴娘子先天不足兼之情绪内结故而药石之效甚微云云。杨楝捉过琴太微的手腕,细细摸着她的脉门,试了半天,忽然觉得其中有异。
众人都知道徵王通晓医术,府中供奉的医婆乃至外头延请的太医,但有诊治不尽心尽力的,很难不被他觉察。6氏见他提前回来,早就吓破了胆子,一个字也不敢多说。杨楝狐疑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缩在一旁那两个服侍琴太微的小宫人,心中纳罕:“难道她根本没吃过药?”
他想起了什么,心中一凉,立刻扳过了她的脸仔细端详。她虽然气若游丝不出一语,盯着他的眼神却十分警觉,这不像是一心求死的人吧……他用手指理了理她的头,转头对程宁说:“拿担架来,把琴娘子抬到虚白室去——此地阴暗潮湿,怎么能养病?”
虚白室却在一水对岸蓬莱山上。因清馥殿房舍狭小,庭院鄙陋,太后便在蓬莱山上择了两处别致的馆,供杨楝读书休憩之用。虚白室是一处临水的别馆,恰在天籁下方,两处有攀山游廊相连,四周林木丰茂,篁竹影动。杨楝爱其清幽,便做了一处小书房,偶尔也过个夜,所以一应床帐陈设都是现成的。这样的地方让给一个小妾养病,倒令众人都暗暗吃惊。不一会儿就有担架过来,众人七手八脚将琴太微抬下,用被子裹得密不透风。琴太微只剩一口气吊着,一通折腾差点晕死。杨楝又密嘱陈烟萝等人一路跟着送到岛上,不可有一点闪失。
俟他们都走了,杨楝在床边坐下,探身寻找,果然从小被子下面摸出一只白瓷小水盂来,里面尚有残留的褐色药汁。原来她当真不肯吃药,全都悄悄倒在了水盂里。杨楝仔细闻了一下药汁,辨出其中并不只有方子上那些药材,心中大震。他沉思了一会儿,先回书房另写了一个药方,嘱咐人立刻煎了。又着人唤了程宁回来,交代了一番,命他拘住那个医婆秘密拷问。然后才来得及坐下喝了一盏茶,又换了衣裳,慢慢往虚白室去。
小小的别馆里站了一地的人。原来琴太微初入徵王府,众人只道她是犯了忌讳才被勉强纳下,洞房时就跟徵王闹得不欢而散,虽是淑妃表妹,似乎除了坤宁宫也不见有人来探问,倒听说太后十分不喜。凡此种种缘故,众人都不愿搭理她。如今徵王忽然为她大动干戈,倒像当真看重似的,一时间谁敢怠慢了。
“她是病人,哪禁得你们这么多人围着。”
杨楝皱眉道,“除了近身伺候的,旁人都回去吧——烟萝你把他们都带走。”
琴太微见杨楝走近,略支起身勉强说了一声谢恩。杨楝俯在她耳边,轻声问:“为何不肯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