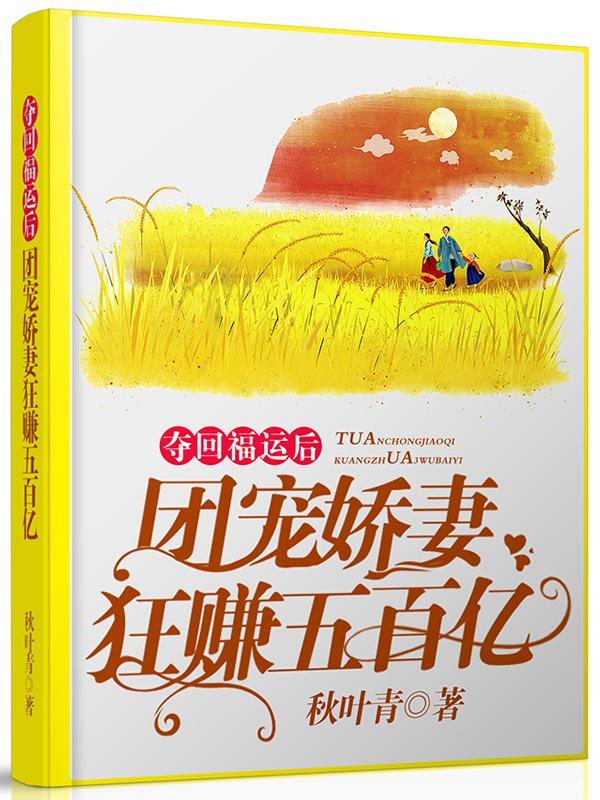69书吧>明日不再来 德农 > 第28节(第1页)
第28节(第1页)
“是吧。”
他满足地笑了,“你媳妇儿也喜欢吃。”
“她也来过?”
“我们群里的人都来过,我带他们来的。刚开始一个个都可不愿意了,说我小气,带他们来这种小地方,吃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能吃。”
“你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我家就住这儿附近,这条街上的东西我都吃过。”
“你不住在别墅里?”
“那儿离市里太远了,不方便。我在这儿有个小公寓,常年住在这边。”
他有两个住处,这就更可疑了。
也许是他那句你媳妇儿也喜欢吃刺激了我的食欲,我一共吃下八个生煎,外加一碗粥。
“现在我们去哪?”
回到车上,我问他。
“去我家。朋友肯定要知道彼此的住处,对不对?”
这正合我意。就算他不说,我也要想尽办法弄清他住在哪里。
他家在临街的一栋楼里,楼门口正对着马路。四楼,房间很小,进门是一个窄过道,左手边是厕所,右手边是厨房。尽头是个大房间,朝阳,大概二十五平米。房间里家具很少。一个衣柜,靠着北面的墙。衣柜南面是一张白色书桌和一把黑色转椅。书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水杯和印有铁观音字样的茶叶盒。靠着书桌的墙上挂着一长一短两把日式武士刀。房间正中是一张单人床,床头向西。床和阳台之间,放着一个黑色的单人沙发和一把摇椅。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台液晶电视。电视下面,从北到南,顺着墙根摆着一溜书,大约一米高,一摞一摞的,很整齐。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的房间整洁得过分。
“你的书真多啊。”
“都是垃圾。你随便坐。我换下衣服。就在这儿换了,你别介意。”
我坐到沙发上,继续观察他的房间,除了整洁,找不出其他的奇怪之处。
“看见那两把刀了吗?”
他一边换衣服一边说,“我爸就是用那把短刀自杀的。”
我不知道如何回应这句话,只能用敬畏的眼神默默地看着那把刀。
“你喝什么?有啤酒和可乐。”
他换好了t恤和短裤,走向厨房。
“我不渴。谢谢。”
“你确定什么都不喝?”
他在厨房里高声问道。
“确定。”
他拿了一瓶打开的啤酒走回来,坐到摇椅上。
“我们现在就开始自我爆料吧。从我开始。”
他喝了一口啤酒,“从哪说起呢?”
他站起来,从书墙上拿了空调遥控器打开空调,“就从虐猫开始说吧。”
他坐回摇椅,轻轻摇动起来,又喝了一口啤酒,“说这件事儿必须先说一下我姥姥。从1993年12月12日老太太第一次见到我,到前年的4月2日她去世,这十八年来,她从来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一点不夸张,一句话也没说过。在我离开哈尔滨之前,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她给我做饭,洗衣服,干这干那,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但就是不和我说话。”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得不承认他很会讲故事。
“她有一个小哥哥,兄弟姐妹中两个人最亲近。二战期间,她小哥哥参了军,死于日军轰炸。所以,她恨日本人。我有一半日本血统,所以,她也恨我。这些都是我姥爷告诉我的。当初我妈在日本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她也从来不听,都是我姥爷听。这很荒谬,对不对?”
“你指什么?”
“她可以恨当时开飞机的那个日本人,可以恨当时的日本军队或者所有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或者,就是恨日本这个国家,但是恨所有的日本人就不太对了,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恨我就更不对了,因为我有一半是中国人,而且,还是她的亲人,身体里有她的基因。她刚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孩儿,我懂个屁啊,但她就是恨我,拒绝和我说话。长大之后,我试过和她讲道理,她不听,扭头就走。而且,你知道吗,在其他事情上我姥姥是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但在这件事儿上,她一点道理也不讲。就像前几年抵制日货砸日本车的人一样。我姥姥也抵制日货,你用不用日货她不管,她绝对不用,她家里也见不得日本牌子的东西。如果你带日货进她家了,让她看见了,她马上就把你的东西扔出去,一点情面也不留。这一点我妹妹最没记性,两个ny手机和一台笔记本都让我姥姥给扔出去摔坏了。我姥姥很节俭,但摔起日货来,那真叫一个心狠手辣,不管多贵,一点也不心疼。”
他自顾自地笑了,又喝了一口啤酒。
“姥姥很有性格嘛。”
“老有性格了。她的故事可多了,今天就不讲了。现在开始说我为什么虐猫。我为什么虐猫呢?”
他停下来,看着我,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