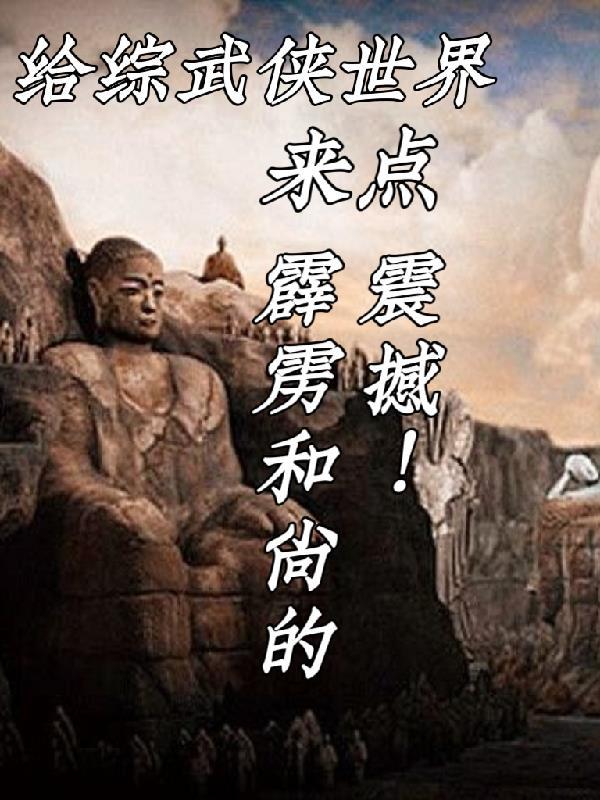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君刹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她生的太过好看,让我不由自主地自行惭秽,脖颈上坠着的玉佩又逼迫我挺直了腰杆,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刻在心里。
在管家的催促下,杨周雪从侧门进去了,我盯着她的背影,心里止不住地羡慕。
如果没有谢氏的从中作梗,像她那般高高在上又众星捧月的人生,原本是属于我的。
我不甘地想,她凭什么用倨傲的态度看向我,不对我道一声抱歉也就算了,甚至没有分给我身后的谢氏一个额外的眼神呢?
很快我就知道了答案。
我跟随着管家穿过长廊,走进正厅的时候,随着我从未在冬日里感受到的温暖一起扑面而来的,是一个年逾不惑却体态丰盈的少妇。
她将刚迈过门槛的我搂在怀里,身上传来的香味跟马车上的熏香一般无二,眼睛却往我的锁骨那儿看,眼眶在一瞬间就红了。
“你受苦了,我的儿,你受苦了。”
少妇不停地重复。
我知道我锁骨那儿有一块小拇指大小的青色胎记,将军府会认回我,自然不只是靠一块玉佩。
大多数人都知道胎儿的胎记容易褪去,因而一直没有对杨周雪的身份起疑。我却不一样,锁骨上的那块胎记就像刻在我骨子里的自尊和倔强,多年来没有失去一点颜色。
少妇的力气太大,箍的我有些难受,可我没有挣扎,我伸出去拥住她的腰,心满意足地想,她是我娘。
杨夫人的拥抱比谢氏的温暖、坚定,衣服上柔软的绸缎也是谢氏缝缝补补的补丁怎么也比不上的趁手。
我原本沉溺在母亲的拥抱里不愿撒手,一抬眼却看到一旁站立着的杨周雪脸上露出了一个堪称刻薄的冷笑。
这个笑容让我的满腔热血一瞬间就冷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无论我表现出的欣喜,还是我身上过于单薄简陋的衣服,都与周围的精雕玉琢格格不入。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我循声看过去,穿着官服的男人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脸看向杨夫人的目光却温柔了不少:“夫人,让明月坐一下吧。”
我知道这就是我的父亲,忠国公杨旻。
杨夫人松开了了我,抹着眼泪坐了回去,杨周雪依旧站在她旁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就好像我有多稀奇似的。
仆人给我端了个椅子,让我坐下。
我坐下后才注意到谢氏跪在了旁边,她衣衫褴褛,从袖口里伸出来的手指冻得通红,一张煞白的脸上早看不出管家嘴里曾经沉鱼落雁的娇贵模样,扭着头看我,尖着嗓子喊我的名字。
于理,我应该恨她,恨她出于私心将我偷换出府,在小巷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十七年,让本应享受荣华富贵的嫡女成了低人一等的女乞,谁都可以踩一脚,一不留神就会冻死在京城的隆冬。
于情,我却忍不住心软,我想起她还没怎么疯的时候,我发了高烧,在夜里含含糊糊着说冷,她红着眼眶说对不起我,握住我的手都在颤抖。还有无数次不知出于真心还是愧疚的维护,她总说,我们娘俩要相依为命啊。
“她就是谢氏?”
杨夫人挑起眉问道。
我攥紧了扶手,不知道该不该应答。
管家弯着腰上前:“是。”
“如果不是明月迫于无奈暴露了身份,我们还不知道要被瞒多久呢,”
杨夫人冷笑道,“偷夫家的钱养男人,偷窃财物,调换嫡庶女,这三项罪名,按律都能杀头了,怎么,你这么急着跟你早死的父母见面?”
杨旻一言不发,他的五官冷硬,看向谢氏的目光格外淡漠。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名门贵女说话也会这么尖酸刻薄,一句话就能将人身上的皮扒下来,带着彻骨的毒。
谢氏疯疯傻傻地朝我笑,她伸出手想抓我的衣袖,杨周雪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口的:“既然父亲早已将谢氏休弃,那又何必再惦念着分文不值的夫妻情?赏她一百板子,若她能熬过一百板子,赶出府就行了;熬不过去,那便将尸首扔到城外的乱葬岗,也是她没活下去的福气。”
她的声音清凌凌的,说起话来轻言细语,格外好听,可字字句句都无比恶毒。
我震惊地看向她——那是她亲娘啊!
“那便按阿雪所说的做吧,将谢氏拖下去。”
杨夫人伸出手抚摸着杨周雪的手背,“摊上这样的亲娘,你也受罪了。”
谢氏被两个人高马大的仆人拖了下去,她“啊啊”
地叫了起来,大睁的眼睛像被捕猎后的小鹿一样,满是茫然。
将军府里明明用了地龙,我却感到遍地生寒。
杨周雪带着笑意的眼睛直直地看向我,她不惧与我对视,不急不缓地道:“罪不及子女,更何况那时我与明月姐姐还在襁褓之中,父亲与母亲既然认回了姐姐,还请看在我十七年承欢膝下、你们又养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能在将军府里留我一席之地。”
杨家
杨夫人露出了心疼的表情,她明明是回答杨周雪的话,眼睛却盯着我:“那个时候你又知道什么呢?杨家既然养了你这么些年,自然不会将你抛弃。明月既然回来了,那你与她便都是我的女儿。”
原本还有些热闹的大厅一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知道他们是要我一个态度,要我认了杨周雪这个妹妹,从此跟她一同承欢膝下。
我咬着牙,只觉得不甘。
在没看到杨周雪前,我总在心里想着一个被当成嫡出养大的庶女又能有什么本事,就算在将军府养的千娇万贵,也改变不了出身的低贱,总不至于会将我比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