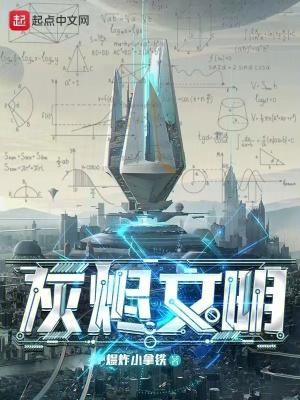69书吧>云中白鹤的意思解释 > 第101章(第1页)
第101章(第1页)
阮如玉弯眉,“阿兄,不是男女有别吗,我要是拉了你这只手,你还有命活过今晚吗?”
阮文卓板着脸,“你上不上,不上我可走了。”
他说着,一把将阮如玉拽上马车,车夫扬起鞭子赶马,阮文卓随手将剑立在一旁,问道,“方才我要收拾那小子,你拦着我做什麽?”
“我新官上任,朝服还没穿热乎呢,万一这个当口有人说咱们阮家恃强淩弱,仗势欺人,岂不是一件麻烦事。”
阮文卓不屑,“说就说呗,我揍他们一顿就都老实了。”
他说着,睨她一眼,“如玉,我怎麽觉得你这官当得还不如不当,成天想这麽多,累不累啊。”
半晌,阮文卓没听到阮如玉的回应,他侧头看去,却见她倚着车壁,双眼微阖,看样子已经睡着了,他轻叹一声,“如玉,你这又是何苦呢。”
辟寒
入夜。
街市空蕩,门户岑寂,一阵阵策马疾驰声踏破稀薄夜色。
宫门口的侍卫们看着迎面沖来的一人一马,慌忙持刀拦住。
“何人在此喧哗?你难道不知道这是禁苑重地吗?若想活命,还不速速闪开!”
马上的那人滚下马背,鼻涕一把泪一把,“不好了!霍老将军去了!”
侍卫们听闻这个噩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乱动。
禁卫军统领王赫正在附近巡视,闻声快步赶了过来,“怎麽回事?”
“王统领,你在这里就好了,要不我都不知道该怎麽办了。”
王赫认出此人是兵部尚书霍宁的亲兵郭万里,忙扶起他,“你别着急,有什麽话慢慢说。”
郭万里哽咽不止,“霍老将军前些日子不是病了吗,他戎马半生,无儿无女,只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霍老将军病了之后,他那个侄子也没影了,将军之前救过我的性命,拿我当儿子一样看待,所以一直是我侍奉将军汤药,今晚又到了将军服药的时候,我叩了两声门,可屋里却迟迟无人应答,我担心出事,就推门进去了,这才发现将军已经去了!”
王赫一惊,“不是说老将军只是吃多了,积了食吗,怎麽突然就——”
“是啊,午后我还陪将军下棋来着,谁承想竟是最后一面!”
郭万里哭得悲切,王赫也不由得有些动容,他拍了拍郭万里的肩膀,转头吩咐一个侍卫,“快去回禀陛下!”
侍卫垂首,应声而去。
王赫忙又补充,“霍老将军为国征战多年,如今骤然去了,陛下听了一定难受,你说得缓些,别惊着陛下。”
“是。”
怡梦宫。
莲弦宝珠白釉熏炉中点着可以驱邪的辟寒香,气味萦然,经久不散,烛光洒落红罗璎珞斗帐,山花焦叶的锦绣纹络斜映在榻上女子的脸上,随着忽明忽暗的烛火轻轻曳动。
贾太后睡得不踏实,她悠悠转醒,擡起眼皮,凝望着烛台上那抹影影绰绰的浅淡昏黄,半晌,她披衣起身,赤着脚走到鸾凤烛台跟前,擡手从发间摸下一支金耳挖簪,用指尖挑着去拨弄红蜡烛芯儿,榻上的任归睁开眼睛,撑头瞧着贾太后的一举一动。
任归在贾太后身边也有一段日子了,他渐渐知道了这个女人并没有看起来那麽勇敢无畏,她怕黑,每天晚上都要点着蜡烛睡觉,她有时候还会做噩梦,会在惊醒的那一剎那紧紧抱住自己,每当这个时候,他总会不由自主地忘记她大梁太后的身份,把她当成一个普通女子。
任归皱了皱眉,不知怎的,这些日子他同贾太后相处下来,已经没有了最初那麽强烈的恨意,不行,这绝对不行,他用力甩甩脑袋,试图将那点莫名其妙的情感全都抛诸脑后。
贾太后听见身后的动静,回首看他,语气难得和缓,“对不住,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任归愣了一下,他没听错吧,她t刚才居然对自己说“对不住”
?
他心绪複杂,久久不能言语。
此刻,她披着淡粉色的宫装立于灯下,烛光曳在白皙的脖颈之上,仿佛一朵出水芙蓉,与白日里的冷峭狠辣不同,她三千青丝晕着莹莹烛辉,眼角眉梢尽是温柔,与寻常女子无异,完全不像记忆中那个手握生杀大权,动辄要人性命的太后娘娘。
任归望着这样的她,心中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贾太后见任归不作声,又是一笑,“你怎麽了?”
任归摇摇头,“没事,你怎麽不睡觉?”
金簪被火烤得发烫,贾太后将金簪随手搁在一旁,缓步走到了任归跟前。
“在等人。”
“等人?”
任归挑了挑眉,“什麽人?”
贾太后闻言,嗤然一笑,她的眼底一半魅色,一半森然,如同火光般忽闪不定,她扬袖捧起任归的脸,盯着他的眼睛,轻声说道,“好奇心害死人,你不觉得,你问的有点多吗?”
任归的心颤了一下,他何尝不知道自己方才失言了,他自住进怡梦宫以来,一向隐藏得极好,他怕她起疑,所以她不主动告诉他的,他从来不会多嘴问上半句,可是今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来的底气,忽而擡手握住了她的素腕,执着道,“如果我一定要问呢?”
任归手心的温度和金簪一样烫,贾太后下意识地缩回手,却被任归攥得牢牢的,她细眉微挑,轻斥,“松开。”
任归不仅没有松手,反而加重了手上力道,他将她拽到怀里,“告诉我,我想知道。”
贾太后垂眸瞧见自己腕上的红痕,笑容一下子冷了下来,“放肆!你信不信,哀家即刻就可以下旨杀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