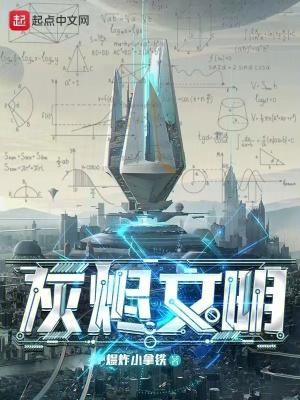69书吧>渡亡经全文阅读原文 > 第99页(第2页)
第99页(第2页)
他紧了紧手臂,&1dquo;我爱你,可以不顾一切。”
所以爱qíng也是需要时间长大的,他是国师,清心寡yù了一百多年,没有爱人的资本。他关心国运,关心天下苍生,唯独不知道应该怎样让一个女人快乐。他和她的爱qíng,始于他百无聊赖的逗弄,谁知欺负着、欺负着,把自己赔进去了,真是天意。他在爱qíng方面不比十几岁的少年老练,偏偏这么青涩的心理,搭配上老掉牙的年纪,于是开始倚老卖老,觉得自己有能力netg消灭于无形。结果他输了,输得那么难看,一败涂地。
他做错了很多次,这次要好好斟酌,不能再只顾自己了。她倚在他怀里,猫儿似的温顺,他把她送进卧房,她湿漉漉站在地心,仆婢让她入浴,她拒绝了,&1dquo;找身gan衣裳来换了就好,还有国师的换洗衣服,让人现在就准备。”
公主府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男人的衣服。还好昙奴那里有压箱底的陪嫁,借来一用正好。
把人都支出去,面要伺候公主更衣了。她坐在烛火下,光1uo着身子背对他,那窄窄的纤细的身条,脆弱得撼动人心。他束起她的头,拿簪子绾起来,绞了热手巾细细给她擦拭,她顺从地听他指派,不管他怎么搬弄,她都一力配合。他把她转过来,看着她高耸的胸脯,有些不好意思。莲灯却很大度,笑了笑道:&1dquo;这半年长得很快,我以前羡慕巫女,现在不必了。”
他到底抵御不住诱惑,红着脸说:&1dquo;我想靠一下。”
她的耳廓辣辣烧起来,腼腆道:&1dquo;随便你呀。”
他所谓的靠一下,其实是想淹死在里面。他把脸埋在双峰间,即便喘不过气来,也没有抬头的打算。
莲灯抱住他,心里涌起温柔的1ang。他虽然活了那么久,有时候还像个孩子。她捋捋他的头,想起那位国师来,便问他关于他的近况。
他说:&1dquo;他的元神本来就依托在那半部经书上,丹书铁劵没了,他的神魂便无主了。行尸走rou一样,活着也是折磨,索xing把他的两魂bī出来,让他暂时安定下来。”他抿唇一笑,&1dquo;别谈那些事了,说起神宫就会扰了好心qíng,不谈也罢。”
他放轻了手脚替她穿上明衣,那柳色的纱罗隐约映现出她肩臂肌肤的嫩色,他满意地打量,赏心悦目。
他看由他看,反正她不想同他分开。牵他安置,手脚密密地缠住他,扬起脸说:&1dquo;你不会走,对不对?”
他抚抚她的脸,&1dquo;我不走,你好好睡吧!”
她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他怀里睡着了,他心头却乱得厉害,盯着那盏红烛直到天明。
早上起netg神奕奕,他却赖在褥子里不肯起来,她也纵着他,自己在妆台前傅粉点面靥,回头望了他一眼,温声道:&1dquo;我要进趟宫,多谢陛下的好意。盛希夷那里请他代我婉拒,不能耽误了人家。你好好歇着,等我回来。”
暖金色的锦被间露出他的半张脸,睡眼惺忪,&1dquo;早些回来。”
她应了,绾好髻回来亲了他一下,&1dquo;别起来,接着睡。”
她宠爱他,真就像公主对面。他有些好笑,支着头看她悄声吩咐仆婢,起netg后给国师吃什么,穿什么,面面俱到。然后回身对他一笑,出门去了。
彼此都小心翼翼,害怕伤害对方分毫,越是这样,越让人心酸。他仰在那里听脚步声渐远,直到消失,略卧了会儿便起身,去前面的院落找昙奴。
昙奴知道昨天他们冰释前嫌了,虽然有些难过,也还是替他们高兴。
他脚下踯躅,一反常态的吞吞吐吐。昙奴见状把人都遣开了,拱手道:&1dquo;国师有话不妨直说。”
他站在一株花树下,温润的五官,这次竟没有距离感。他说:&1dquo;本座来拜托娘子一件事,昨日我和莲灯的尾,娘子应当已经知道了,其实并不是真正和好,是我的权宜之计。当初我让她吞药,不过是要她听命于我,后来的种种,你也知道了。到如今本座时日无多,不能让这个药害她一辈子。”说着复一叹,&1dquo;我明白她的心,她是舍不得我,可我不能那么自私。我想让她忘qíng,给她解药她不接受,只有来托付娘子。”
昙奴看着他,起先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位不可一世的国师,也有如此成全别人的心。活不长久,就不应该再牵绊住她,作为旁观者,她是赞成他这么做的。
&1dquo;国师只管吩咐,我尽我所能。”
他点了点头,把net官送来的药jiao到她手里,&1dquo;请娘子为我想办法,务必让她服下。”
服药不难,可她也担心,&1dquo;这样违背她的意思,我怕最后反倒伤害她。”
他说不会,&1dquo;她会忘记一切,从遇见我开始,忘得一gan二净。我知道一再抹去她的记忆,美其名曰对她好,其实伤她至深。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最后一次,你也希望她过得无忧的。”
昙奴犹豫再三,那颗解药掂在手里,千斤重似的。她怅然望他,&1dquo;国师当真下定决心了?”
他垂眼说是,&1dquo;今日起我不会再踏出神宫一步,以后还请娘子替我照应她,临渊这厢先谢过了。”他说完肃容,恭恭敬敬对她行了一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