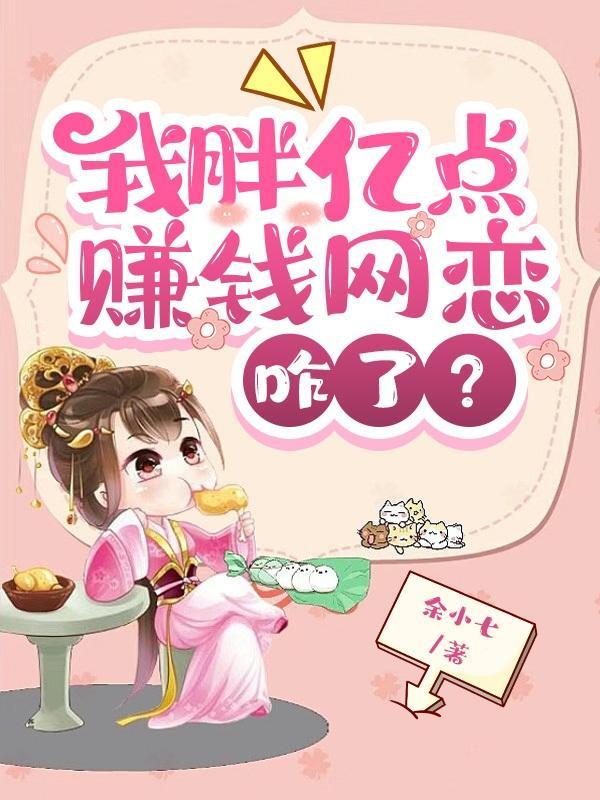69书吧>摆地摊的苦日子 > 第83章 送饭(第2页)
第83章 送饭(第2页)
郁风打头阵,一身重孝,引导着队伍开启了第一次的“送饭”
之行。
刚走了几步,老会计小跑着走上前来,悄声对郁风说道:“腰弯着一点走,不能站得那么的直。”
是啊,考妣之丧!哪能雄赳赳,气昂昂地呢!
通常情况下,那副哭丧棒由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或是孙子拿着的,但郁风是老郁家的第三代单传,又还没有子嗣,那一付哭丧棒只好由他自己拿着了。这一路上,郁风的双手已经用来捧托盘了,只能用双臂一边夹着一根哭丧棒了。
紧跟其后的是安琪,大白天提着一盏煤油灯。灯罩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三个字:渭水堂。
再后面就是小妹。
小妹刚跟在安琪的身后向前走,老会计现少了什么东西,示意小妹停下。转过身去,向着后方高声地喊道:“小妹的饭准备好了没有啊?”
“早准备好了!”
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嘈杂的人群后方传了过来。
“赶紧拿过来啊!”
老会计急急地说道。
只见一个中年妇女端着一个饭碗,从人群的后方走了过来。
老会计对小妹说道:“你用衣角兜一下饭。”
小妹用手拽起了外套的一角。那个中年妇女将一小撮热饭倒在了小妹提起的衣角处。
到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地准备妥当了。
老会计对已经停下了脚步的郁风说了一声:“可以走了。”
由郁风打头,一长列戴着白帽子,披着长长白布条的队伍在阵阵锣鼓声中,浩浩荡荡地逶迤而行。
队伍的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后面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整个队伍拖拖拉拉,缓缓而行。这边,郁风都已经快到村庄的中央了;那边,处于队伍最末端的才从家里出。队伍最末端的都是父亲的平辈,甚至于是长辈,他们是常服,走了最后面。
郁风一路徐徐而行,满脸的庄严。手上捧着的那只托盘越的沉重。
每年的除夕,开饭之前,家家都要带上鱼肉去村里的土地庙上供上一供。都是父亲带着郁风去的。郁风从来没有想过,会有那么一天,他得披麻带孝的领着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地前去土地庙。
农忙时节,郁风经常给父亲送钣。那是送到田头,而不是送到土地庙。他再也看不到父亲狼吞虎咽地吃饭的样子了。这一顿饭已是阴阳两相隔。宁隔千山,不隔一板。过了明天,他将永远地见不到父亲了!
两只手捧着托盘,胳膊里还要夹着两根木棍,这个姿势挺不好受的,还要走那么远的距离。郁风一直将那只无比沉重的托盘端得稳稳的,从未倾斜过;两只胳膊里的“哭丧棒”
一直夹得紧紧的,从未滑落过。
郁风的脑子里,已经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那么僵硬地机械地走着。好在这条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就算是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
父亲的形象,与父亲有关的陈年往事就象是快进一般,飞快地闪现着。
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然而这一切只能在脑海里浮现了,再也听不到父亲的言语了!想着,想着,郁风的眼泪,禁不住地刷刷刷地流了下来。眼泪模糊了郁风的视线。
此刻,郁风腾不出手来擦眼泪,就让滚滚的眼泪那么无声地流着!
郁风的思绪飞快地运转着,眼泪哗哗地流淌着。在不知不觉之中加快了步伐。很快,长长的“送饭”
队伍就脱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