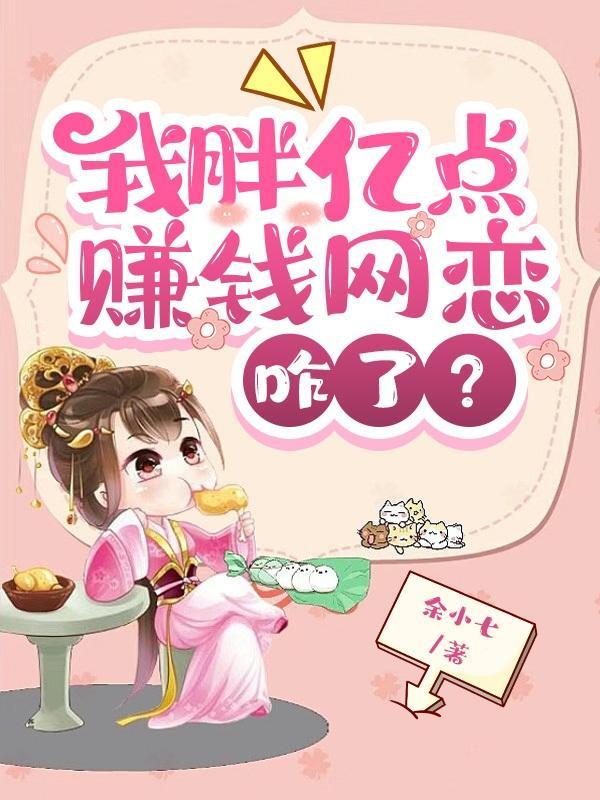69书吧>岁时有昭(双重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 > 第56章(第2页)
第56章(第2页)
顾长晋垂眸问她:“夫人昨夜睡得可好?”
容舒不着痕迹地吸了吸鼻子,踮起脚给他理衣襟,笑意盈然道:“妾身睡得很好,难怪郎君喜欢睡这儿,这罗汉床果真是舒服极了。”
是么?
这罗汉床就铺了一层极薄的褥子,躺上去硬邦邦的,周遭还没得床幔,压根儿拦不住风。
她那拔步床毡垫、炕毯、床褥、靠背、迎枕一应铺陈应有尽有,跟小半个屋子似的。
这罗汉床同她那张精致的拔步床压根儿没得比。
这么个连漱口的水都要加竹盐与花露的姑娘,真能觉着这样一张罗汉床会舒服?
顾长晋神色淡淡道:“夫人喜欢就好。”
这娇花似的姑娘,他倒是想看看她能在这儿坚持几日。
第二夜,容舒如昨日一般,依旧是踩着他熄灯的时辰来到书房,只这回她让人往书房里搬了七八盆银丝碳,把整个书房烘得温暖如春。
夜里她睡得倒是规矩了,一动不动地抱着她的月儿枕,侧脸对他。
翌日起来给他更衣时,脸上还印着道淡淡的印痕,轮廓瞧着同她月儿枕上那只桂树上的兔子还有些像。
如此过了十来日,上元那日,一场透骨奇寒的暴雪侵袭了整个北境。
那夜上京气温骤降,那七八盆银丝碳不顶事,她睡到一半又钻入他的被窝里。
这次可就不仅仅是把脚丫往他裤管里钻,手也摸到了他的里衣内,在他小腹上摩挲。
顾长晋半夜被摸醒。
若不是确定这姑娘是因着冷在睡梦里找热源,他差点儿要以为她骨子里藏着个登徒子。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揪着她的袖摆将她的手扯开,而后便听“哧啦”
一声,她那单薄的用天蚕丝织就的里衣就此被他扯出了一道口子来。
小姑娘这下是醒了,懵懵地坐了起来,低头摸了摸右肩裂了一道长口子的里衣,抬眼望他:“郎君为何撕我的衣裳?”
语气里是浓浓的疑惑,若是细听,还能听出一点儿责备。
雪光在漆黑的屋子里映出一地霜白。
小姑娘披散着一头浓密柔顺的发,里衣松散,露出了半副藏在里头的靛青兜儿。
漫天雪光仿佛都拢在了她身上,那白玉般的肩头与肩上那颗针尖大小的朱砂痣被那艳艳青意逼出了几缕香艳旖旎。
顾长晋蓦地睁开了眼。
书房里窗牖半开,梧桐树枝擦过棂木,伴着秋风飒飒作响。
没有雪,没有火盆,也没有躺在身侧的小娘子。
是梦。
意识到这点时,顾长晋察觉到了自己的异常。
他自幼习武,瞧着文质彬彬,实则体魄强健。只他惯来清心寡欲,不曾有过甚旖旎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