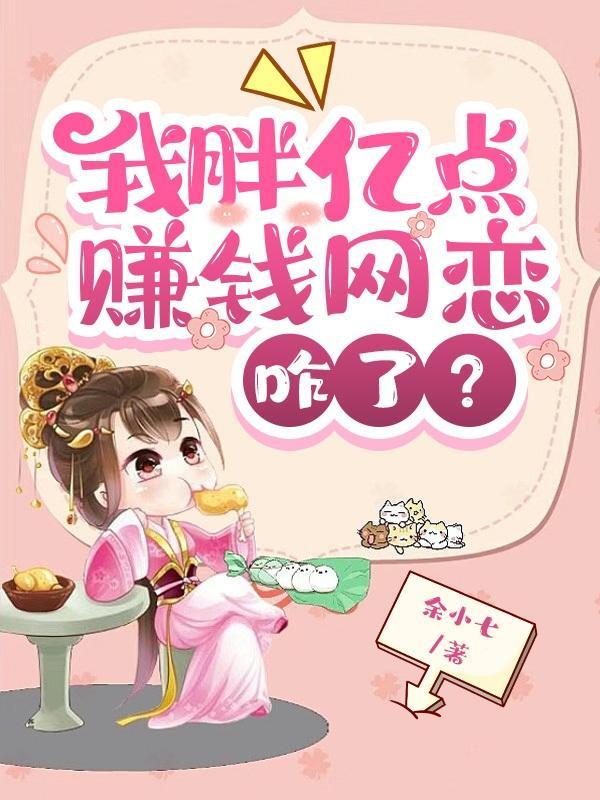69书吧>be文求生指南快穿第二部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谢玉弓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梦魇之中。
每一个梦的结尾,都是他的九皇子妃。
她端着盛在?酒杯里面伪装成合卺酒的毒药;或是同面孔模糊的人通奸,在?窃窃私语的诉说着他有多么令人厌恶;再或是她面无表情,将自己推入万丈深渊的冷酷模样。
他在?梦魇之中看着自己一次次因为她而溃败死?去?,容颜枯萎,遭受背叛,又重新变回了那个在?深宫之中苟延残喘的可怜虫。
一次次感受如同?利刃挖心?一般的痛苦,最后他在?被?人骑着当成狗一样在?地上爬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向了三年?前的庭院处,那个同?白珏站在?远处树下,朝着他看过来的工部尚书?的庶女?——白榆。
她面上带着笑?意,哪有半分的怜悯和叹息,满满的都是嘲讽。
谢玉弓爬行的动作一僵,突然生出了将背上骑着的十?二?皇子?,一下子?掀开,甚至是活活掐死?的冲动。
因为在?“白榆”
的注视下,谢玉弓现自己再也装不?下去?了。
他的隐忍和蛰伏变成了刮骨钢刀,将他“凌迟”
得体无完肤。
他羞耻得面红耳赤,恨不?得将四肢尽数蜷缩在?一起,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谢玉弓不?懂。
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梦魇之中,每次面对白榆的注视,无论白榆带着什么样的神色,他都会有种无地自容般的慌张。
白榆的目光宛如炙热的熔岩,每一次看向他,都会烧灼他的皮肉,烫伤他的骨骼,再融掉他的皮肤。
让他化为一滩淋漓滴落的血水,从马车里面的缝隙滴答逶迤了一路。
马车?
哪里来的马车?
谢玉弓在?一个坍塌的梦魇之中醒神,看到了那天随她归宁,他们一起坐在?马车中的样子?。
她捡起了自己膝盖上的蜜饯,当着他的面,缓缓地放进了口中。
谢玉弓当时并没有和白榆对视过。
但是在?这个梦魇中,他们对视了。
谢玉弓看着自己膝盖上的蜜饯,被?一只纤细柔美的手捡起,而后送入了一双嫣红的口唇之中。
唇齿在?他的面前闭合,那一双生着两颗小痣的美丽眼睛,映着他一身蟒袍,银面遮脸的模样。
而后谢玉弓就觉得,被?投入白榆口中的,不?是那颗蜜饯,而是自己。
像遭遇了油炸和火焚,谢玉弓低下头,他看到自己在?白榆的注视下,正在?融化。
浓黑的血水顺着马车的缝隙滴滴答答流走,先是双足,这样他便无法行走,不?能再离开她半步。
而后是双臂,这样他便再也无法做出攻击她的举动。
再然后是躯干,直至内脏外露,代表他一腔无处掩藏的心?肺,胸腔的每次跳动收缩都在?她的注视之下。
可她无动于衷。
她怎能面对这样的自己还无动于衷?
她似乎有些奇怪地看着融化成一副骨架的躯壳,又看向那颗依旧在?疯狂跳动的心?脏,而后她对上谢玉弓已经开始融化的双眼。
谢玉弓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头颅只剩下一双无法从白榆身上挪开的眼睛。
然后他看着自己,在?她的注视之下,走向毁灭。
她的双眼是灌满了谎言的带有剧毒“溶金水”
,谢玉弓被?她融骨化肌,却在?她的注视之中,在?她微微开启的艳色口中,蚀骨销魂。
她像一株曼陀罗,毒性散的前期,甚至感知不?到痛苦,只是口干热,心?跳剧烈,就像是——春心?萌动。
当你?意识到有毒时,已经是再也无可挽回。
有毒的,谢玉弓在?梦魇之中呢喃。
“有毒的!”
白榆在?一群守在?门口的侍卫之中,亮出了自己的九皇子?妃玉佩,好容易挤进屋子?。
屋子?里一个老太医,正在?给谢玉弓包扎。
而谢玉弓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胸膛□□,胸腔的起伏剧烈而急促,这便是中毒的前兆。
说来有点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这一次原本是七皇子?自导自演的刺杀。
但是七皇子?的计划被?二?皇子?的人知道了,七皇子?是太子?的人,二?皇子?表面上也是太子?的人。
但是二?皇子?自己也想做太子?,于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自己私下里打着太子?的名号,笼络了许多人为己用。
七皇子?的计划被?二?皇子?套出来之后,他便准备伺机打压太子?党。
因此七皇子?的“救驾”
,注定要失败,因为二?皇子?在?他“不?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