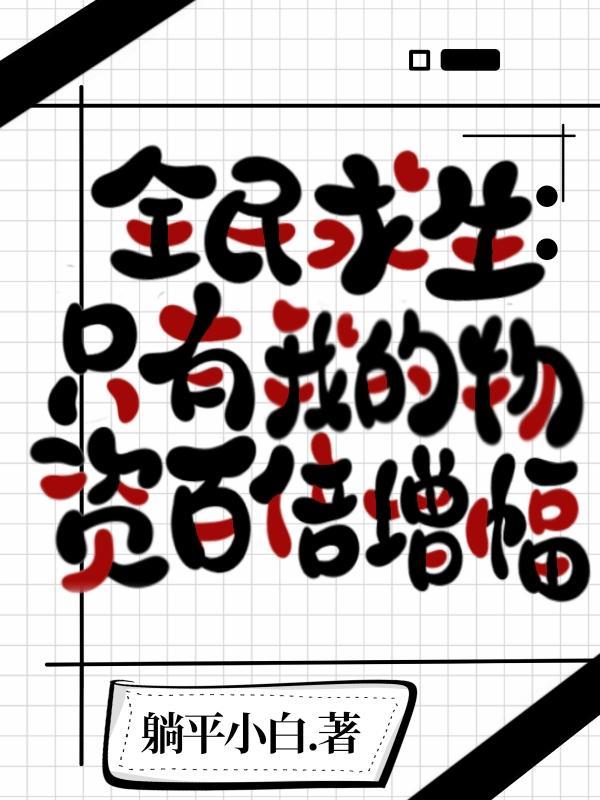69书吧>锦衣郎为什么指唐明皇 > 第六十章给你解闷(第1页)
第六十章给你解闷(第1页)
车内坐着的,正是定远候的嫡妻,墨家的主母。
是了,能调动戍城卫兵力的,可不仅仅是他的父亲定远候。她的母亲,已故的太皇太后的义女,又是手握重兵的秦氏的嫡女,如此尊贵的女子,这世上除了当今太后以外,再难找出第二个。
女子身着深绯色锦绣华服,头上饰以花钗,纤细的手腕上,却挂着一串檀木的佛珠,与这富贵的打扮格格不入。她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仍是能让人一眼便惊艳的相貌,只有眼角一些细小的纹路,暗暗透露了她真正的年纪。
她声音不高,却不怒自威:“闹够了,便在你父亲亲自来找你之前,随母亲回家。”
少垣听了她的话,一改适才的狂躁,沉默地揽起衣袍,爬上马车。
他坐至女子身边,垂着头一言不。
车内的气氛无比沉默,二人皆不一语,桌上放了一个香炉,正燃着袅袅佛香。
走到半途,少垣才垂头丧气地伏上自己母亲的膝盖,闷声开口:“母亲,是我将少微给逼走的。寻常我总是找她的麻烦,也总是在萧砚面前说她的坏话,还为萧砚退亲笑话她,可我……并没有想要害她。”
他只是见不得她同别人亲近,见不得有别人对她好。祖父不可以,萧砚也不可以。他不想让她嫁人,甚至想,她若是嫁人,那她还不如死了算了。可是,她真的被父亲责罚,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又不舍得她死。
那是他唯一的姐姐。
女子抚上他的头,声音十分冰冷:“她既然离开了墨家,墨家便没有这个女儿。她是生是死,都是她的命。”
少垣身子重重一颤,自她膝上起来,难以置信地望着她:“母亲,连你也这么说?”
他原本还有一肚子话要说,但看到女子的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眼前的女人,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端庄,岁月不曾在她脸上留下刻痕,仿佛也不曾在她心上留下任何痕迹。她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母亲,她依然是那个尊贵的、受万人敬仰的秦氏嫡女。
他不再同她亲近,负气一般道:“她是少微,是我的姐姐,除此以外,她没有别的命。”
在戍城卫骑兵的护卫下,车轮一路向北,穿过杭州府,朝官道驶去。
秦暮羽将车幔拉开一角,目光在车外停住。
这条街再往里去,过两个街口,便是杨成万的府第。
她乘坐的这辆马车,很快就会将这条街抛到身后,她会将车幔放下,会将已经到喉边的“停”
字永远地吞下去,她会表现得像一个硬心肠的母亲,仿佛她从来不曾嫁人,也从来不曾,有一个被她抛弃的女儿。
沈寒溪的马车刚走到杨府跟前,便接到一个帖子,正是他这几日在等的消息。哑巴被差去周府送信,宋然则陪同温氏在花园里闲逛。她此前崴了脚,只能慢慢地走。忽见一个锦衣郎迎面走来,停在她跟前:“宋姑娘,大人请你陪他去见个人。”
宋然眼皮一跳:“现在吗?”
那锦衣郎道:“现在。”
宋然不知沈寒溪打得什么主意,但又无法推脱,只好同温氏道了抱歉,要随他过去。
温氏却拦下她,道:“陪大人见客,可不能穿得这么素,劳烦这位大人等等,我带宋姑娘去换件衣裳。”
宋然本想说没那么多讲究,却碍不住温氏一腔热情。那锦衣郎知道女子出门要比男人讲究,默默等在门外。
温氏将她按在梳妆镜前,捡起她乌黑的,语气中不无艳羡:“这样好的头,若不好生打理,便白白浪费了。”
她幼时时便常为家中的姊妹绾,许久不练,有些生疏,但梳出来的髻却依然有极高的水准。望着镜中那可人的模样,她满意地点点头,拿起珠翠为她饰在间。
见她对着镜子有一些失神,温氏不禁问道:“宋姑娘,你在想什么?”
她敛了眸子,唇边有寂寥的笑意:“我在想我的母亲。”
温氏笑吟吟道:“令堂也时常替你束吗?”
她摆弄着一支玉兰的簪,良久,才轻声道:“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六岁那一年。如今,却已经有些记不得母亲的样子了。”
温氏只当她是没了母亲,一时满心爱怜地望着她。
沈寒溪还在马车上等,也不好多做打扮,便只结了髻,淡淡地扫了娥眉,换了一件外衣。好在她底子好,寻常不讲究穿戴,已经常常让人多看两眼,如今简单修饰一番,更是娇妍可人。
连那等在门外的锦衣郎眼中也不小心流露出了惊艳之色。
温氏目送她离去的背影,轻声叹了一口气。手轻轻抚上自己的小腹,苦涩地想,若是腹中的孩子还在,说不定,也是一个乖巧聪慧的女儿。可惜这个孩子,同她没有缘分。
宋然寻常低调惯了,冷不防又穿回这锦绣衣衫,微微有一些自在。好在沈寒溪尚在同她冷战,自她坐进来,便没怎么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