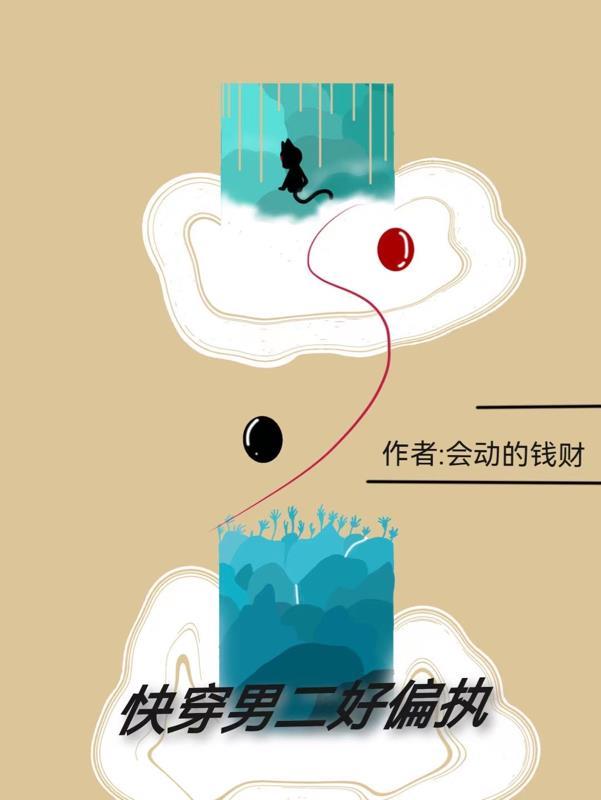69书吧>锦衣郎为什么指唐明皇 > 第九十七章浮生若梦二(第1页)
第九十七章浮生若梦二(第1页)
延寿八年,谢家遇到了多事之秋。先是谢老爷子病故,再就是在宫中为妃的谢贵妃,因小产薨逝于那一年的九月初九。在遍插茱萸的时节,谢七先后失去了父亲,和与他一母同胞的姐姐。
自那一年开始,政局也开始逐渐生变化。
圣上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内阁中的辅臣为争夺辅之位,明争暗斗闹得很欢。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谢二公子,因政见常与当时的内阁重臣相左,又过于刚直,数次被进谗言,惹来圣上的不满,不到一年,便被贬谪三次。
整个谢家都嗅到了危机,无论是五姑娘的小产,还是二公子的坎坷仕途,都有着同一个源头,那就是,圣上对太后娘娘的忌惮,终于殃及了整个谢家。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变故,便足以扭转一个人的一生。
终日在外游荡的谢七,在那一年回到家中,帮助打点族中事务。
宋然记得,他到尧州寻自己时,是一个下雪天。
彼时,距离她被家族孤零零地抛在尧州,也快要满三年。寒冬腊月,她住的偏僻小院,有一枝寒梅独自盛开,厚厚的雪压在上头,几乎将枝条压断。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冷的冬天。谢七坐在屋内,望着她吭哧吭哧地搬来一个暖炉,又去找府上的婆子索要生火的碳。那些丫鬟婆子都势力惯了,钟伯在时,她们尚且还忌惮着他是夫人的心腹,钟伯不在,她们便换了嘴脸,恨不得拿鼻尖瞧人。
她点燃暖炉时,谢七的目光落到她冻得通红的手上,问她:“如今这样的生活,是你打算过到何时的生活?”
她抬眸看他,几年不见,他的眼角眉梢依然堆着缱绻的风流,可是那微笑时会有桃花盛放的眼中,却是白茫茫一片雪色,那让她欣赏与羡慕的纵情与恣意,仿佛也都堕入凛凛寒冬。
见她不回答自己,他将手伸向暖炉,一边烤着火,一边道:“侯爷还在物色合适的女婿吧,想入赘墨家的子弟,应当是不缺的。若是慢慢挑,兴许也能挑到一个比萧砚好的。运气好了,他能与你举案齐眉,可万一运气不好呢,他现自己娶到的是一个在墨家毫无地位的小姐,冬日里甚至没有足够的炭火取暖,他是会怜惜你,还是会瞧不起你?这些事,你可曾想过?”
她将手拢到嘴边哈着气,轻轻敛了眉:“自然……想过啊。”
谢七的肩头披着雪白毛领的裘袍,唇角一直挂着淡淡笑意,说出的话却有些恶毒:“青楼妓子尚且会为自己打算,努力攒银两赎身,或者努力攀一个好男人。你出身世家,有出众的相貌,有满腹的才华,难道就甘愿一辈子困在别人为你安排的生活中吗?”
他的这番话,自然早已在她的心上过了无数遍,要问她甘不甘心,她自是不甘心的。可是不甘心又如何,这墨家是一个巨大的牢笼,墨这个姓氏,便是加诸在她身上最大的枷锁。说来也讽刺,祖父为她取名少微,便是想让她如那天上的少微星一般,避开纷乱复杂的人和事,淡泊自在地过这一生。可是她却无时无刻不被人情世故所困,在墨家,她只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通过装乖讨巧,才能换取片刻的安宁。
她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识时务,看眼色。她不能太聪明,也不能太笨拙,她要在适当的位置上,不能出风头,也不能犯一点差错。
“哥哥,这些年,我过得有些累。”
她低眉,气息在半空遇到冷意,化作缭绕的白气。
将指尖搓一搓,轻叹道:“这么漫长的冬天,何时才能到头啊。”
他望了她很久,将一只手的掌心翻起,那是一只五指微张,修长有力且形状好看的手。
“过了这个冬天,便跟我来,好不好?”
他的声音平静地像是窗外正在飘落的雪片,里面没有一丝蛊惑。可就是这么平静的一句话,让她瞳孔微微放大。那个时候,她想,她不能等谁来救她,她得自己做出选择。
半晌,她把手交到了他的手中,轻轻地承诺:“好。”
他为她伪造了身份,带她避开墨家的耳目来到陵安,提出的条件却简单——他只要她的人,留在陵安。
上一次他救她,对她并无所求,可是这次不一样,他要她有所回报。
“我需要你做的事,时机到了你自会明白,你是个聪明的姑娘,自然也会知道,你该怎么报恩。”
他骑乘在马上,身后是铅灰色的天空,树木还保持着向上生长的姿态,光秃秃的枝杈斑驳交织出冬日的萧瑟,有寒鸦停在较粗的横枝上,冷眼注视着他们的别离。
“再见时,你我立场或许会截然不同,少微,你要自己保重。”
如今想来,分别时的这一句提醒,应当是他能够给予她的最后的怜悯。
随沈寒溪去杭州时,她已隐约察觉到,谢七与她遇到的这些事,冥冥之中有某种联系。可是彼时,她尚未看到事情的全貌,一直无法将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连在一起,也一直不愿相信,那桩桩件件都似偶然的事,皆与他有关。
如今,他口中说的那个时机到了,她才终于明白,自己也不过是,他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