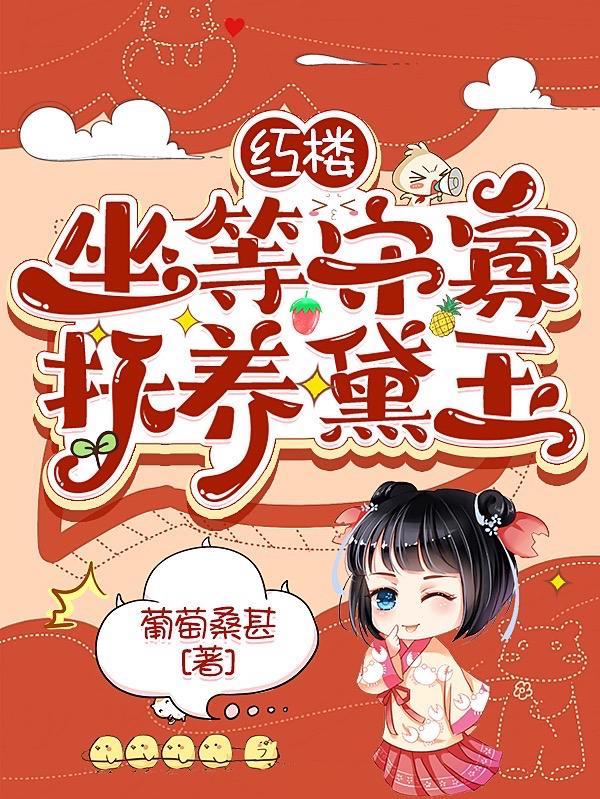69书吧>死对头穿成我的猫by草履免费阅读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从头顶蹭到脖子,再蹭锁骨,蹭得满身缎子般的猫毛上全是烟味,蹭得谢松亭皮肤泛红,微微渗汗,躺在地上摆烂地不再挣扎。
他被蹭得痒了,脸色红,耳鬓的黑狼狈地贴着脸,被抬起头的缅因从上往下俯视。
它不会说话,就用行动证明,如果你要抽,那我就蹭,看是抽一手烟先病,还是抽二手烟先病。
谢松亭叹了口气,妥协:“……我不可能一天就把这烟给戒了。”
缅因仍然不退。
“半年?”
缅因低头,看样子又要蹭。
“三个月?”
其实被缅因蹭还挺舒服的,只是谢松亭不习惯。
温热的。活着的。有力的。
贴着他。
像被眷顾了。
他深知自己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与其被拿走之后伤心,还不如从未陷落。
毕竟这不是他的猫,是席必思的。
虽然说了是植物人,但他要是醒来了呢?
都的医疗资源数一数二,这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很大。谢松亭不想在自己还猫时表情难看得像哭丧。
缅因这才满意,在他胸口趴下来。猫的体温和重量将他的思绪拉回,意思是答应了他三个月内戒烟。
谢松亭:“你知道自己快七斤吧?”
缅因施舍地给了他一个眼神。
“你要压死我?以后再胖点就不准……”
缅因低头舔了他锁骨一口,把他“上来”
两个字舔回喉咙。
第一感觉是热,像被烫热的东西贴了一下,接着是湿意,最后才是一点倒刺带来的阵痛,很快那点阵痛也过去。
谢松亭身体比脑子反应快,像捋什么恶心的东西一样捋开它,仓促翻身,看也没看猫就逃进卧室,砰地关上了门。
棕虎斑被甩在地上,老神在在地晃晃尾巴。
不疼。
下次还舔。
谢松亭还是出了卧室。
快递即使在雨天也十分敬业,把席悦给他的快递送到了家门口,砰砰敲他的门。
“德邦快递!”
谢松亭打开门,看向门口叠放在一起的两个巨大木箱,问:“这都是我的?”
“谢松亭先生不是吗?您看看,上面写着这两个都是您的。这是订单,您在这签个字。”
谢松亭问:“这两箱运过来得多少钱?”
其中一个一看就是新来的,没什么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