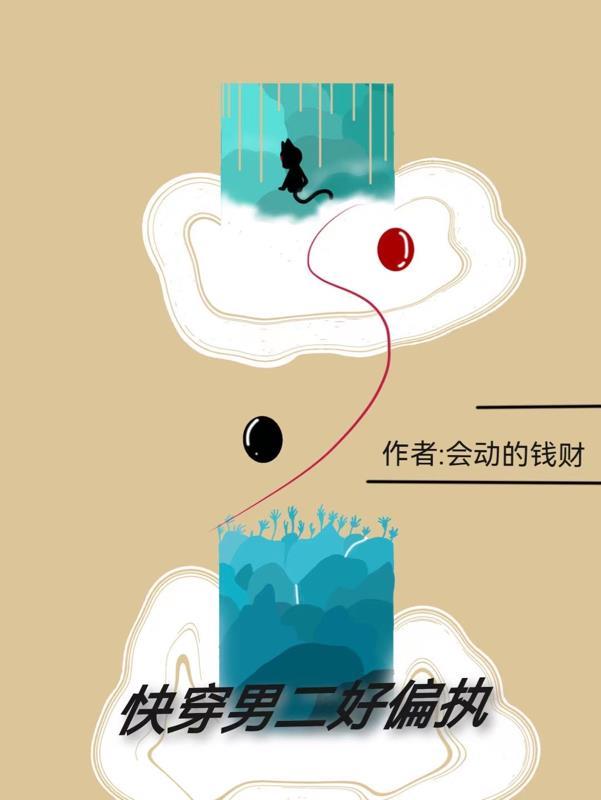69书吧>重生之渣夫狠妻全文免费阅读番外 > 第45页(第1页)
第45页(第1页)
冷酷的黑衣公子,杀人不眨眼的黑衣公子,惹得西陵鹤近来总是对我黑着脸的黑衣公子。
说到赴宴,还是要说说俞琼华。一月前我得救后的第二日,俞琼华便洗去了往日的掩饰,露出她的真容来。
那是天山化雪一般的容颜,那是不沾染人世间半点烟火气的清逸。我忙里抽闲作乐,整了两句酸话,将其美略述了一二:人世碌碌众奔忙,赏美猎色夜未央。忽见凡尘落仙子,驻足难舍弃旧芳。
这个驻足难舍直不再将别个放在眼里的,正是西陵鹤。想那日人家不曾露出这人见人爱的模样时,他是半点也不将人放在眼里的,谁曾想,第二日一见了人家的真容便木了半边,亦不再将我搭理,只是说:“如此的人物,怎可屈居于下人之列?便是官宦人家的小姐,也不如她。”
我闻言,直觉地心叫个劳什子搅碎了,硬是说不出话来。是以只能在闲极无事时作了这么首酸词儿来表一表我的情怀。
世间负心男子何其多!西陵鹤连只把我当做亲生的妹子一般的看待的话都说将出来了。
可是,谁家的兄长会常和妹子同枕席呢?谁家的兄长会常和妹子又亲又抱呢?谁家的兄长会常对着妹子喊媳妇儿呢?
变心便是变心了,何必如此?光明正大地说将出来,我敬他是条好汉!
既然他要这般羞辱于我,我何必要成全他?是以我说了句话,一句让我为千人骂众人怒、叫西陵鹤不得意的话,这句话就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为着不叫她薄命也得带回府中护着,免得什么猫啊狗的惦记得慌。”
这句话说得极到点子上,西陵鹤他还真就惦记着。这一月来,他不仅不曾来找过我,连音书都绝了!倒是俞琼华常提着他,说他进来又做了些什么事,夸他如何聪颖。
他也不想想,他今年才十三岁,人家俞琼华都十七了,能等得及他么?若是他恋着宿山月还有一线机缘,毕竟宿三月只大他两岁,倒也可等一等。
罢罢罢!
有这想法还是因为我知道宿三月此女,她喜欢的决计不会是比她小的男子,决计不会喜欢不霸气的男子。所以啊,她叫我放心啊。
偏生此时我不止不如意,简直是大大的不如意。这便算了,每日晚间像是有什么老鼠盯着我,直叫我发毛。点了烛看时,却又看不见甚么。是以我疑心鬼怪。
我此时事事不如意,醋缸子又翻了,心中酸得厉害,自然不能叫罪魁西陵鹤如了意。是以,决计不能再留着俞琼华了。即便西陵鹤移情后,我伤情归伤情,到底不愿作贱自己,不愿再和他纠缠,可我的度量却没这许大,叫他伤了我的情后还能事事如意。
是以,去给干爹贺寿这日,我也带上了俞琼华。干爹向来受众人尊敬,来贺寿的人多,公子什么的自然也多,到时我只消不将俞琼华乃我家婢女的身份说破,而是说成我爹新近收的干女儿,自然能一箭双雕。一是为俞琼华觅个好归宿,二是断了西陵鹤的念想。
然而事情总是要出乎我的预料。
到宿山月家时,大家都热热闹闹的,我念及爹对俞琼华的多番夸赞并西陵鹤的背弃,心中颇是不像意,只是将俞琼华推给我的好友——知县家的嫡女叶长青,便自家寻了个僻静处,指望自家一个人赏赏月,去去郁气,哪曾想就看到宿山月和那救过我的男子称兄道弟地说话。
我后知后觉地想起那日黑衣公子眼叶不眨地将人脖子抹了了的事,腿一软,差点跌坐在地上。我情急之下只得抓住了廊柱,撑着站定。
谁曾想,我一点响动都不曾露出的,就叫那月华中的两位翩翩儿郎惊觉了。
“谁?”
一声带着冷意的厉喝,正是那黑衣公子的声音。我暗暗地劝了劝自家的腿要争气,不许在他们面前跌倒,才信步走将出去,在他们面前站定:“是我。今晚的星辰当真亮得紧,二位好兴致。”
我佯作淡定,其实心中早已万马齐奔腾,踏得我的小心肝喷洒出万千血雾。
许久不见宿山月,我忒想与她诉一诉,我当真的看见了男子的那个物事。虽然那个是与我继母的物事,好歹是真的。此件事我一直不曾和别个说起,闷在心里怪难受的,现下好容易见着了宿山月,不诉一诉我的心就像是猫爪子在挠一般。
人生谁没个伤情的时候呢?在这里伤了情,大可不必在这里沉溺,只消将心思移在别处,只当着伤情的事就是那埃尘,过些时日风吹一吹也就散了。不去刻意想起,便也不大容易为之伤情了。
唔,总之,这埃尘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若是我总惦念着,还有几时的快活几时活命呢?
唔,这些个事儿不能深想,想深了这情便伤得狠了。
我毫不萧瑟地站在他们的面前,轻言浅笑。黑衣公子眼中含了笑,生意如玉石相撞的清越,却又低沉得叫人喜欢。他说:“我晓得。爪子够利。”
我点点头,宿山月便来揉了揉我的头发:“许久不见你,怎地不来找我?”
我能说我被西陵鹤气着了,一月里只闭门钻研医道,谁也不曾见过么?
我笑笑:“进来对世事参悟了一番,在房内修身养性。”
宿山月嗤笑道:“再修身养性,那春宫一百零八式依旧叫你记得牢牢的。”
我斜眼睨她:“小妹不及宿兄多矣!”
宿山月厚着那如城墙一般的脸皮点点头:“那是,这多吃的四年饭菜不是白吃的。”
然后我抬头对那黑衣公子道:“我见你年纪长我们许多,定然知道得更多了。”
结果这一句话就揪到了大虫的耳朵,这大虫今日想来也是要修身养性,是以不曾如那日对那尼姑一般眼也不眨地将我送去阎王的老家,只是淡淡地睨了我一眼,笑道:“息夫小姐煞是好逗。”
我好逗么?逗我好玩?我脸黑了,终于知晓往日西陵鹤对着我脸黑是个什么想法。
我闻言也不怒,只是浅笑道:“如此,不过只及得上你之万一罢了,当不得什么。”
他也不怒,只是看了我一眼,便不再说话。
宿山月轻轻咳了咳,道:“他便是陆云天。你梦见的那个陆云天。”
我睁大了眼,这这是天上下红雨了么?我调戏了我梦中的英雄?
这真是大大的不该。我拱手,行了个抱拳礼,道:“久仰久仰。适才这玩笑话当我不曾说过罢!”
说完,我还悄悄地瞅了一瞅宿山月,这丫头分明是要叫我在我梦中英雄的跟前儿失态啊!好在我修身养性十余年,早已成了精了,不曾出得丑来。
陆云天点点头,那俊美冷冽的脸孔上带着些儿笑:“听闻你左眼角下一蝴蝶展翅欲飞,为人亦如蝶招眼自在,果然不假。”
而后我欲再说时,他又道:“人见过,陆某先别。”
等陆云天走后,我才拉着宿山月问:“他怎地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