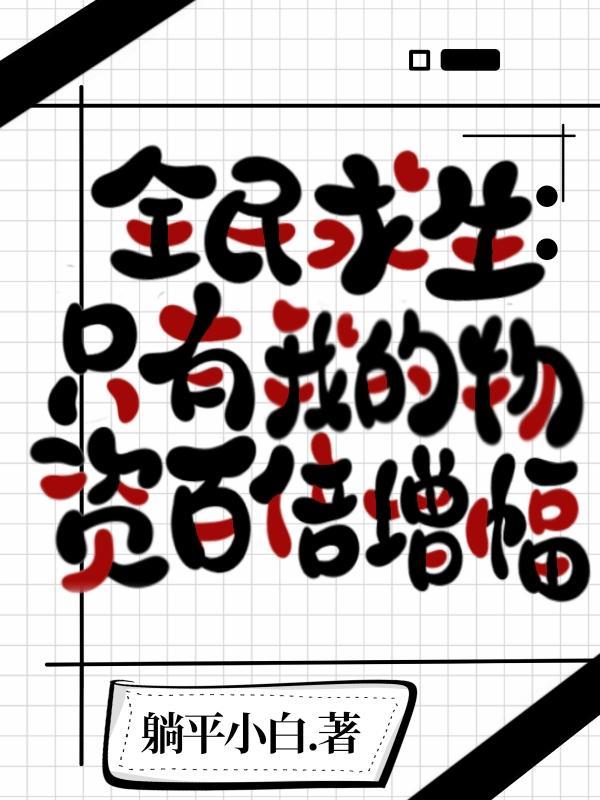69书吧>重生之渣夫狠妻全文免费阅读番外 > 第50页(第2页)
第50页(第2页)
爹立马收了那张冷脸,陪笑道:“这是说的哪儿的话!俗语有言,黄金棍棒下才能养得出有出息的儿女,我这也是为她好。”
俞琼华似笑非笑地看了眼爹,那双美目只怕把爹的魂儿都勾了去!她微微笑着对我招手:“到妈这边来。难为雅娘了。当初我引火自焚,只当这辈子便这般去了,不曾想天可怜见,叫我仍旧留有性命。我一醒来,便在这个躯干上了。后来遭难,辗转道了空林寺,现下才得了机缘和你们团聚!”
我不肯过去,她一行说,一行使手帕子拭泪。她的说辞倒是有些理,若非如此在空林寺时她为何要担着险救我?且她之所言我在梦中也曾见到过梦中我是林剪秋,死后不也没到阴曹地府见阎王么?
然这也仅是说得通罢了。并非说得通,这般荒诞无稽之事它就是事实。
我看着俞琼华,淡淡道:“此事颇荒诞了些!”
爹此时在旁却是青筋暴起,碍于俞琼华在,他并未抄起茶杯扔向我,而是将之掼在了地上,哐当的声音如一个榔头敲在我的脑仁儿上,生疼生疼的:“无知的业障!这些年我是怎么教导你的!连生母都不认了!”
俞琼华此时在一旁使着有些沙哑淡淡声儿凉凉道:“八年不见,脾气倒是见长了!”
爹在一旁附和:“就是,欠教训!”
俞琼华看着爹语噎:“我说的是你。”
爹的气势顿时便消减了,只在一旁坐着,不说话。
俞琼华看着我,收了泪温柔地笑道:“雅娘将将才出生时,眼角左下处便带了蝴蝶形的红色胎记,还是我说去请会画画儿丹青大家竹山青刺将出来的咧。你两岁时,有次才一会儿不见西陵家的阿鹤,便哭着闹着就是不肯消停,等他来了才好呢。”
话将将才落,她又哭将起来。
我抬起头笑道:“这些事儿但凡是我家的旧人都知道,都能如数家珍。且我三岁前做过甚事儿,我年纪小,哪里就晓得?”
爹看见俞琼华这一哭,眼睛便肿得和桃儿一般,很是心疼,立马便喝道:“无知的蠢东西!快些儿叉出去!”
我点点头,连情也顾不得伤,立马就回了我的房里,叫青黛拖她兄弟找人给我使。
青黛因问我:“找人做甚?”
我淡淡地:“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继母做事的,你们放心,这是对你们的主子只有好处,做得好了,指不定你们的主子还能回来也说不定。”
青黛闻言脸上的笑滞了一滞,强笑道:“小姐这是说甚话儿?”
我却不愿再和她们多言,只是挥手叫她们下去。”
尔后我去了西陵府,和西陵婶子说了会子话儿,等到西陵鹤从学中回来了,和他去了他的院子,使了他的衣裳穿着,去找宿山月。
西陵鹤因问我:“这又是怎地?”
我摇头道:“俞琼华留不得了!咱们去找宿山月!”
西陵鹤看着我,有些不大乐意:“找她做甚?”
我闻言,也是!何须我再大张旗鼓地跑一趟?于是我道:“这般也好,阿鹤,叫你心腹的小厮去告诉阿月一声,叫她查查俞琼华的来历!我就不信,这般的一个人,会当真如她现下看着这般干净!”
然而此时西陵鹤却狞笑道:“雅娘要查谁呢?俞琼华?哈哈哈哈哈”
“有趣!有趣!实在有趣!西陵兄当真叫我们看了一出好戏!”
走进来的是宿山月,她脸上的笑当真的像花儿一般艳丽!此时此际,她已然换了女装!其袅娜娉婷之处,足以迷煞万千少年!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们,脑仁儿一阵阵儿地疼,当真的疼。
“啊!!!”
我抱头嘶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