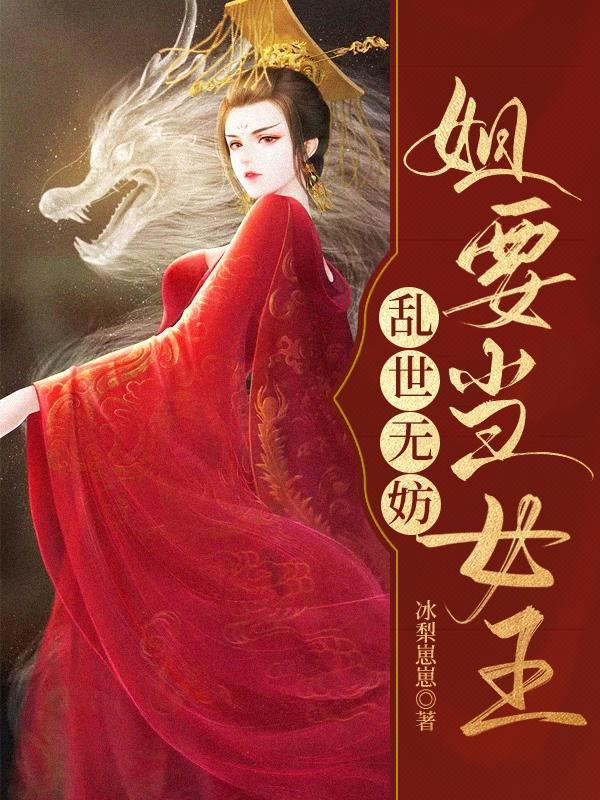69书吧>秦家小日常txt > 第79页(第1页)
第79页(第1页)
“我可从未说过自己是君子。”
秦少芳轻淡地说,如蔓揣摩着这一句话儿,竟是不自觉的走了神儿。
☆、42公子解意,意不由衷
两人便隔了门槛,相望了片刻,仿若许久不见,有好些话儿要说的,可细细想来,却又两厢明了。
似他这般风雅的人儿生来便当如闲云般自在,不能教那世俗所缚了,若是循规蹈矩,就再没有这样好的情致。
如蔓暗自唏嘘了一回,遂打先儿将眸子瞥了开去,道,“不做那君子,便也很好。”
秦少芳见她垂眸轻语,也放柔了声儿,将抹额的缨绦抚了抚,佯叹道,“怎地不是君子,可就进不得你的屋儿了?果然愈发进益了。”
如蔓知他有心打趣儿,便也不计较这许多,叫翠儿去沏了新茶来招呼,自家便大方儿地引他入厅。
因着前些日子告了病,总在东厢养着,未曾多多见客,私下里,如蔓便并不十分讲究,闲时凭栏读书,亦或倚窗绣花,倒乐的清净自在。
木漆桌案上搁了三四册书文,旁边儿摆着一方精巧的圆肚儿紫砂壶,素纱铺盖的案台上,散碎地落了些风干的花瓣子,墨香和着花香,虽只是厅房一隅,却也足以窥得小女儿情致了。秦少芳心下赞叹了,便随手捻起一册书文,但见淡黄的纸页上头,隔行批了些小字,字迹十分娟秀。他略略翻了几页,忽而掀了哏帘,道,“见你于书文上这样用心,我便考你一考,如何?”
如蔓只道他素日里并不喜舞文弄墨,遂有些个好竒,便端端正正地往那角櫈上坐了,歪头道,“难得少芳哥哥赐教,自然是要仔细记下的。”
秦少芳也不推辞,煞有介事地开了腔儿,“你且说来听听,读书为的是甚么?”
“男子读书,为的是胸怀天下事,做一番事业,女子读书,为的是知情解意,不枉做那花瓶美人儿。”
如蔓答得很是干脆。
“如你所言,读书的最高境界又为何解?”
秦少芳并未抬头,只将一片花瓣把玩于指尖儿。
如蔓思量了片刻,便道,“读天子书,识圣贤意,为读书髙境。”
秦少芳并不接话,翠儿新煮了花茶,正巧端了上来。
如蔓只道是自己浅薄,说错了话儿,便间,“可是说的不好,倒让你见笑了。”
秦少芳这才将书本放下了,带上那一贯温和的笑意,只是眸子里好似盈了一汪春水,潋滟不清,他缓缓道,“你说的并没错,也尽是大道理,想来安夫子教导的很好。”
如蔓听他提起安夫子,不由地一愣,旋即扯了笑,说,“少芳哥哥不妨明说,我才能读几日的书,有些道理却是不大明白的。”
“自古古语论天下,有句古话说的最是贴切,”
他仍是那样专注地将如蔓望了,道,“女子无才便是德。”
“原是这句,”
如蔓听了这样的话,真真儿有些失望,原以为他与那世俗之人并不相同,岂料竟也是这样将女子瞧低了,“你竟是这样想的。”
秦少芳挪开了目光,呷了口热茶,道,“我如是说来,并非是看低了女子,恰恰相反,这话儿偏偏就可贵在才德二字。”
如蔓不明所以,就见他淡淡地开口,“世间才智精明的女子,却往往并不能平顺一生,皆因那争胜好强之心,亦被那才德二字所累。男子一生所求,不外乎功名利禄,女子一生所盼,不过是爱侣良人,聪慧便可,但无需十分的精明,白白枉送了身家。”
这一番话儿说的真切,却又似平地惊雷,从未有人这般细细拆解,咀嚼之下,当真是字字珠玑。
但凡世人所求,皆不过若此,竟教他一语点破了去。
细细回味之下,如蔓竟是不能说出一个字来,只觉情真意切,不免有些感怀。
“小五可还误会于我了?”
秦少芳见她小脸儿似添了一抹思绪,便知她心名意了,不枉自己素日待她之心了。
如蔓微微揺头,叹道,“今日听君一言,受益匪浅。”
“你这丫头,怎地这样文邹邹起来了?我倒是不习惯了的。”
秦少芳将书放下了,不消多提。
又想起前日里曾听三哥说起过,秦少芳自小精通文墨,于治学上颇有造诣,可如今却只流连风月,不问孔盂。
如蔓心下不解,遂接着问,“如此说来,少芳哥哥为何不求取功名,好求得一世造化?”
“人生在世,岂能事事都遂了意的?便如同那陈年的酒酿,你明知它醉人不浅,却甘愿醉生梦死。”
秦少芳亦笑着反问,“小五既听我如此言论,日后可还会用心习读了的?”
如蔓点头,“自然要学的。”
“这便是答案,你我都是一样的人了。”
他笑得风雅,可如蔓却见他眉宇间绕了淡淡的无奈,遂举杯道,“那咱们便为做了这一样的人而畅饮一番罢。”
“可此处却无酒。”
秦少芳将杯子晃了道。
“茶可代酒,和着清风鸟语,倒也有几分意兴,自当开怀。”
如蔓先饮了一口,秦少芳痴痴地将她瞧了片刻,忽而举头饮尽,竟是笑得十分爽快。
许是久不曾畅谈,如蔓心下也将之前的不快抛了开去,两人便就着茶水,暍到了传饭时辰。
秦少芳并未在东厢用饭,只说秦婉蓉及笄大礼,不可怠慢了,如蔓知晓他们二人情意笃厚,便未加挽留,送他出了院子。
关了门儿,心下不免有些怅惘,好似东厢也变得空落落的。
回屋儿拿了书来看,却总禁不住想起方才那些话来便再无法专注了的,忽而又是安夫子沉吟的教诲在耳根旁儿萦绕了,搅地她心乱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