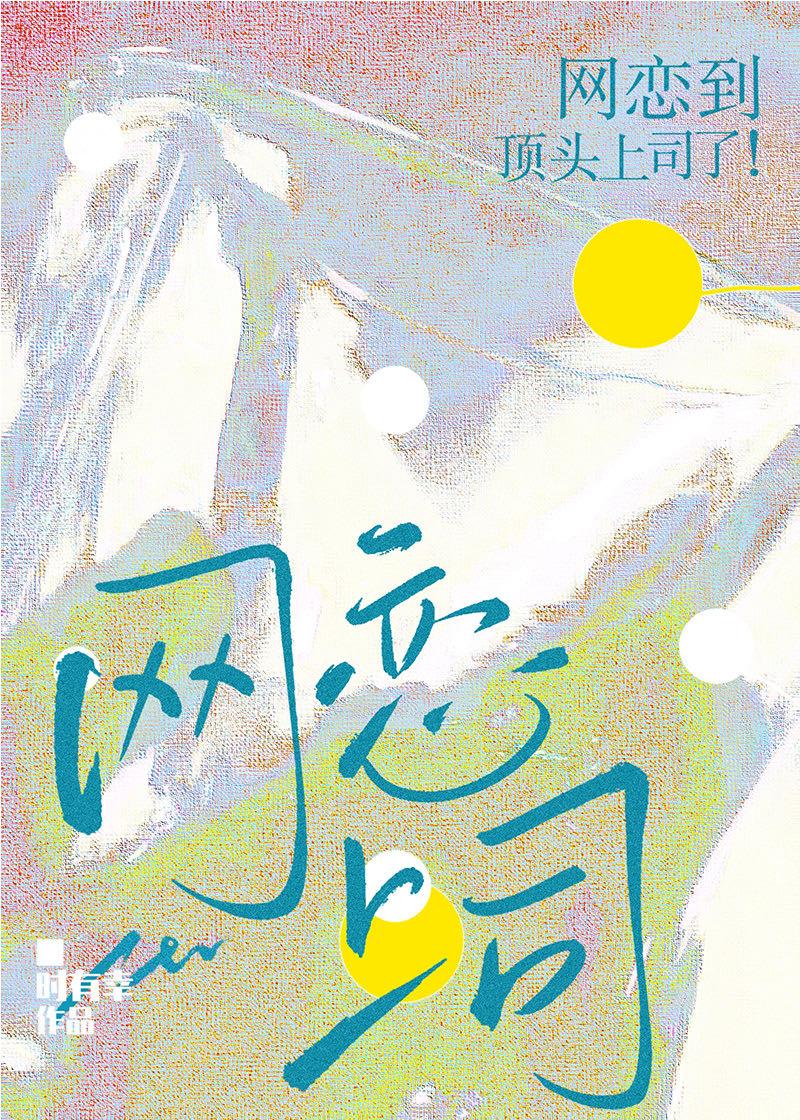69书吧>穿书之豪门男寡TXT > 第68章 第 68 章(第3页)
第68章 第 68 章(第3页)
有些事,还是要再逼紧一点。
片刻后,钟智脸上带着一丝兴奋与得意,兴冲冲地出了门。
家里的贴身丫头问他可回来吃晚饭,他想了想,只说去找朋友喝个花酒,不用为他备饭,只单让小厨房炖点滋补的汤水,晚上回来再喝。
那丫头因与他有过尾,爬过钟智床头,便对他格外关切,自答应着,便让小厨房备了甜汤出来,待到晚上,便一直坐在室内苦等。因等得久了,不知不觉倒在床边睡了过去。
待她忽然间从梦中醒来,才现竟已是第二日的清晨,而六少爷钟智,竟然彻夜未归。
她虽有些担心,但想到从前他亦有过眠花宿柳的经历,倒也并不在意。谁知这又是一天一夜过去,六少爷竟然还是人影不见,丫头们这才害了怕,忙不迭地报了三太太知道。
钟家自然是一阵大乱,四处查寻。谁知整整一天,各处能寻的地方都去遍了,竟然连车带人,都是踪影不见。无奈之下,便只得报了官,并在报纸上了寻人启示。
这六少爷忽然失踪一事,可谓在钟家掀起了轩然大波。
三太太这边自是哭死过多次,也不必说。便连大房太太何意如,也在佛堂里给他念了数晚的平安经。
只是在夜里念经之后,何意如在回到睡房之时,却又悄然望着钟智院子的方向,双手合什,嘴里暗暗道
“既给你念了这许多的平安经,你便平安上路,也不必感觉天凉水冷,有多委屈,自然日后再多烧些纸钱给你,添置些锦衣玉服,也便罢了。”
她这边为钟智烧香念佛,旁边服侍的丫头蕊儿却好像失了魂魄,不仅面色憔悴,倒常常丢三拉四,出了许多素常没有的错。看在何意如眼里,倒也并未指责于她。
只是私下里,那每过几载,便会悄悄来到大太太屋子里商讨贩卖丫头的人牙婆子,便又偷偷上了门来。
蕊儿自打得知钟智离奇失踪、生死未卜后,一时间心里面便吓破了胆。
她虽然不知他究竟是出了何事,可是不知为何,只要一看到太太在佛堂里为六少爷念平安经,她这心里面便七上八下,倒觉得那经文似乎变了模样,竟成了度亡魂的往生经一般。
而且这两日,她更觉自己身上不对,不仅月事未来,浑身更是难过得紧,不仅没有胃口,更是看到稍油腻些的菜品,便会呕吐出来。
这一日她虽然极力控制,却还是在何意如身边服侍时,忍不住呕了两声。
何意如倒和顔悦色,只让她先回去歇息片刻,然后再派了婆子带了她出去,寻个大夫好生看看。
蕊儿一边谢了太太,一边便回了房里,心中只想着钟智,果然看见两个太太常用的粗壮婆子,便来接她出去瞧病。
她心里有几分明白,自己这般模样,极可能便是怀上了六少爷的种。可是太太既让自己去看病,又不得不去,便只得跟着婆子出去,想再做打算。
只是这一去,大太太院子里,从此便再无人见过这蕊儿的身影。
便有人问起来,也不过说那丫头大了,太太心疼她,赏了她外嫁,已择了好人家去了。
二房这边,因钟义与于汀兰早已分房而睡,秋天夜长,他便时常约钟秀到自己房中倾谈。若是偶有雨天,钟秀不便过来,二人也要尽打上一通电话才得入睡。
这日傍晚时分,天上便飘了冷雨,钟义便知钟秀应是不会来了。
他一人熬到夜深,便只觉房中像是少了些什么,终又抄起电话,和钟秀窃窃私语。直至时已夜半,外面漆黑如墨,雨丝纷飞,他竟不知房门微启,已和他分房睡的于汀兰竟悄无声息地摸了进来。
原本这些日子以来,于汀兰的身子情绪,都比前些时日大有好转,一天里倒是明白的时候多,糊涂的时候少了。也正因此,她便更加思念起钟智来。
只不过她也知道,自她被钟义兄妹逼着穿上了守贞锁,更多派了人手监看着她,自己与老六虽在一个宅子里头,见面的机会,却偏偏比登天还难。
且她娘家因父亲被派了异地为官,竟阖家都跟了过去,一时间,当真是孤掌难鸣,四处无援,只能每日里在丫头婆子的看管下,强自支撑。
因这一日,她忽然听到两个丫头背地里在偷偷耳语,隐约便听到一句六少爷已失踪数日的字眼。于汀兰虽未听得真切,但是关心则乱,她又是爆炭的性子,立时便上前抓了丫头的衣襟,问其所说究竟如何。
只是现下钟义派来看管她的丫头,都已经不是她从前的心腹。并且上有钟义的倚仗,下看于汀兰走着霉运,对她早就没了从前的顾忌。见她上来逼问,便根本不去理她。
于汀兰这些日子已经深知这些下人的势利,倒也有所收敛,但是眼下既是听到钟智失踪这样的大事,便不管不顾,疯了般拉扯那丫头,逼她说将出来。
那丫头被她疯癫的样子吓到了,终还是将钟智已经失踪了数日的消息说与她听。她因厌烦于汀兰,也隐约知道二奶奶与六少爷的尾,这工夫干脆添油加醋,便说外面都传闻六少爷风流好色,必是睡了哪个仇家的老婆,被人暗中害了,这些日子都寻不得,大概早就见了阎王。
于汀兰听了这消息,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一时竟傻在了当场。
待到她呆兮兮回到房中后,从午时直坐到夜深,才从恍惚中醒转过来,目光便落在钟义那睡房的窗子上。
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竟然静静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又从被上面翻出一物,揣在怀里,又喷了些“钟桂花”
在身上。
因为自己喷了这香水后的味道,原是老六最爱闻的。
然后这工夫,她便趁着风急雨大,紧握着怀里那东西,便直摸到钟义的房中来。请牢记收藏,&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