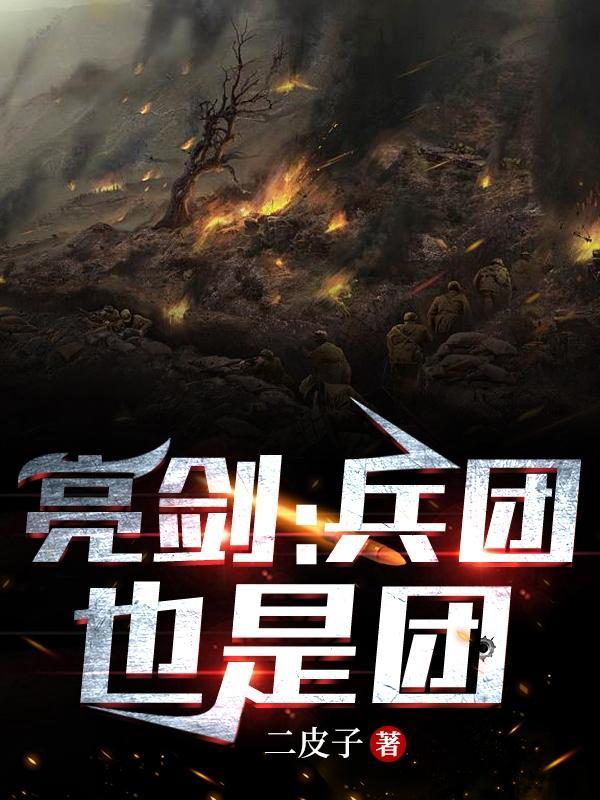69书吧>昭华乱男主是谁 > 番外 婉霜一(第1页)
番外 婉霜一(第1页)
我仿佛做了一场很长的梦。
可是醒来时,我却不太记得都梦到了些什么,只觉得很累。
睁开眼时,我正坐在家中的暖座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拿着书挡住了半张脸。
迎香搬了个小凳坐在我身旁,正捧着一卷书在跟我掉书袋子,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这两日父亲让她教我读书,可我生来就不是那块料,只是为了要让父亲开心,所以不敢忤逆,只能白白在这儿受罪。
迎香最是知道我的,我俩一起长大,她知我不愿学倒也不强迫我,以至于明瞧着我睡着了,她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顾自念完了手里的书,权当是交差。
这会儿她继续聒噪她的,我只管托腮看着庭院里的明媚,想着方才的那场梦。
可跟许多时候一样,我只记得那场梦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真实,
但此刻要细想究竟梦到了些什么,却是难忆万一了。
只依稀记得梦醒前的场景,倒有些骇人。
——我似乎。。。。。。是梦见了自己的碑。
又见一明媚女子眉宇间淡淡含愁,立在碑前祭我浊酒二两,没头没尾地说我护她良多,若有来世要换她护我。
其余更多的细节,凭我想破脑袋也再记不起什么。
我心觉梦到自己碑位是晦气事,于是叫停了迎香对她说
“我方才做了场梦,梦见了自个儿的碑。”
迎香将目光从书本上收回,直愣愣地看着我。
我见她先是锁着眉头,不过很快又听她笑,
“好事啊!人常说梦与现实是相反的,小姐梦见自个儿的碑,可不意味着小姐要长命百岁了?”
我听她胡诌,忍不住冲她翻了记白眼,“你读书多了,没边际的蠢话也是张口就来。我那梦真实得很,按说那么可怕的梦我醒来后该庆幸我还活着才对,可这会让我心里反而空落落的,实在奇怪。”
迎香听我这么说,倒是埋怨起来,“要奴婢说这都要怪大公子。大公子跟着老爷常年在外征战,一年半载好容易把人给盼回来一次,却还总跟小姐讲些他在沙场上的血腥事。那样的事听多了,可不得吓得小姐了噩梦?”
她说得头头是道,可我却觉得不是这个理。
毕竟我从小性子就生得像男娃,年少时总爱缠着爹爹给我讲些战场上的事,后来爹爹封了大将军军务忙碌,我便去缠着哥哥。
本是听惯了的事,哪儿还会被吓着呢?
我正要反驳,突然暖座旁的窗户被从外头推开,我忙看过去,见是哥哥凑进来半个脑袋,耷拉着面孔对迎香说
“你又在背地里说我什么坏话?”
迎香与我一同长大,自然与算哥哥少时的半个玩伴,他俩见面便要拌嘴,我倒爱看。
这不,这会儿迎香也不惧哥哥,反倒冲他扮了个鬼脸,
“奴婢可不敢说大公子的坏话,只是突然想起上回大公子离家时,曾答应要给小姐买了花簪回来,可这都返家五日了,怎还不见大公子将它送给小姐?”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