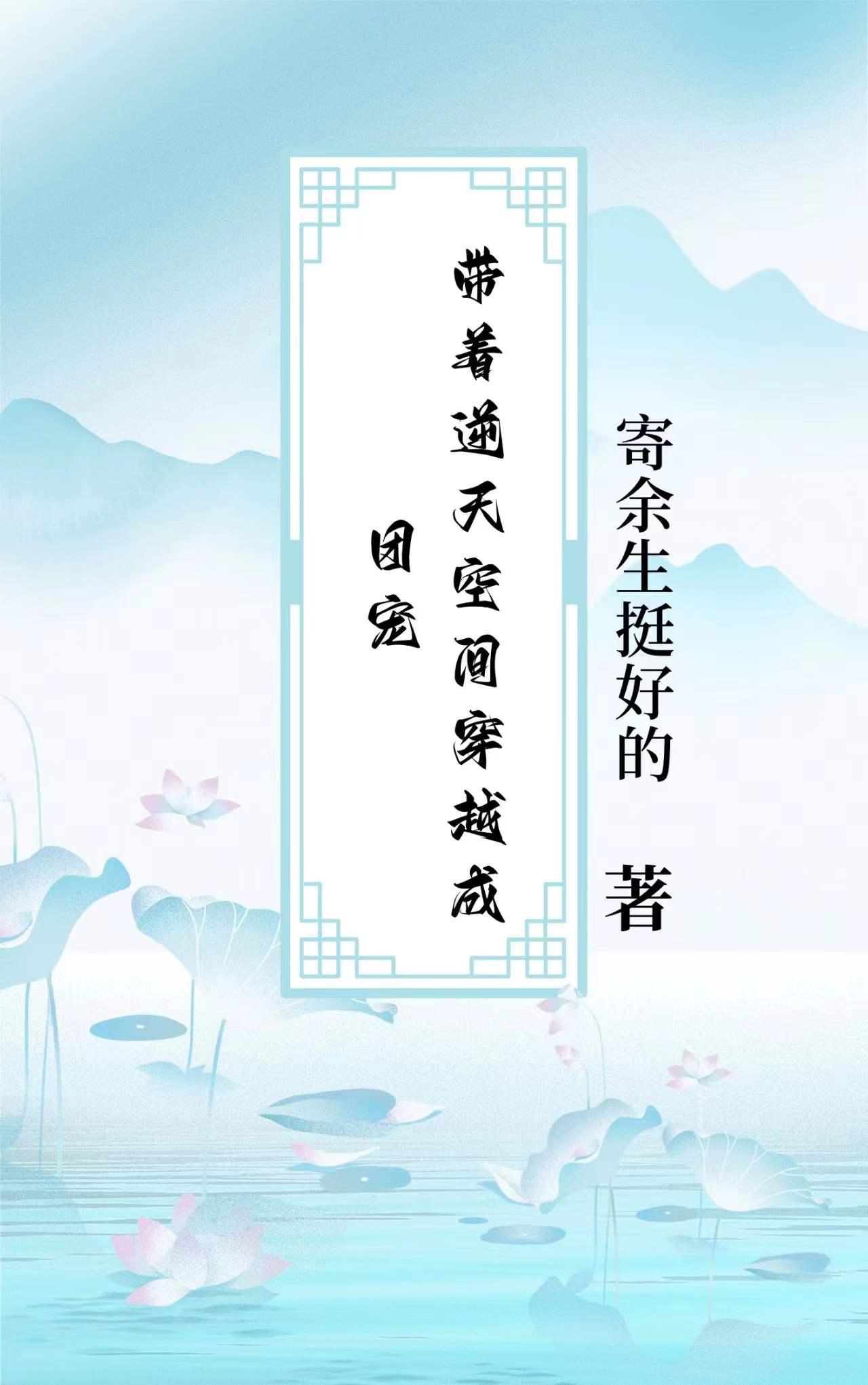69书吧>月亮坠落一千次高清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顿了一下,老周瞥了一眼墙边座钟,又补充道:
“现在过去,正好能赶上散场。”
廿玖
“果然是故意的。”
傅斯乔轻嗤一声,低声喃道。
昨日,他从阮静筠那里得知,她之所以选择了华新理发所,并特意找到找赵明义做头发的背后是有人在刻意「撺掇」,傅斯乔敏感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便立刻将消息告诉给了郑怀。
直到今日晚间,郑怀归来时终于带回了确切的消息,这个诱导阮七小姐的人与此前秘密传递钱宗理所在位置给匡济会的人,确实是同一个。
此人名叫陈晓曼,江浙人士,两年前自上海出发赴法留学,抵达巴黎后经人介绍很快便加入了隐藏在旅欧青年会下的秘密组织。十二月二十日,她与阮静筠同乘一艘轮船抵沪。
至于出生且成长于华北的赵明义,刚好是在陈晓曼远赴欧洲后的那个月回到了国内,而后便在北平工作,直到三个月前被华新理发所聘请,这才到了上海。
单从时间线上看,这两个人的轨迹似乎并不存在什么交集。傅斯乔想不通,郑怀口中「陈晓曼刻意选中了赵明义成为替自己转移敌人侦查的注意力的对象之一」,到底是因为什么。甚至在他看来,他们大概率是没有机会认识彼此的。
闻言,郑怀解释道:
“少爷在英国留学期间,不是曾经与赵明义有过交集吗?”
“确实见过一两次。”
傅斯乔记得,那年,教育基金会突然宣布与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停止发放给他们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许多受惠于这项计划的学生因此陷入生活无靠,求学不能的困境。因此,数百名学生在「旅欧青年会」的联合下,团结在一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夺“求学权”
的斗争。
当时,除了这些本身利益相关者外,为了援助这场「中国学生在法生存与求学」的战斗,另有许许多多在欧洲求学的青年人也自发聚集到了巴黎,傅斯乔便是其中的一个。亦是在这段时期,他见到了作为组织者和他们的接头人,表现十分积极的赵明义。
此人的能言善辩和进度有度,皆给傅斯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后来在将要回国前,知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竟然背叛了原先的组织后,傅大少内心还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我听说,就是因为那时赵明义突然叛变,才导致陈晓曼的未婚夫惨死了在了异乡,连尸骨都没能找回。”
想了想,郑怀继续说:
“所以,我猜测,虽那姓赵的不曾知晓她的名姓,但她却将这份恨意记在心中,一直在关注着仇家的动向,特别是在她将要回国的节骨眼上。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敌明我暗」的关系,才使得陈晓曼毫不犹豫地将嫌疑推到了这人的身上。”
的确,如果真如郑怀所言,有过「旅欧青年会」成员过往的赵明义即便真的被抓住审讯,也绝不可能供述出任何与陈晓曼相关的内容。这对于她来说,当然算得上一个有效且安全的报复办法。
“现下,陈晓曼与赵明义在上海都已经找不到任何踪迹,我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被侦查队秘密抓捕了。”
偏偏此刻看来,作为这两人之间现存的唯一的连接点,负责将「传递密报」这团火,引到赵明义身上的人,似乎就是阮静筠。换而言之,陈晓曼也许早就做好了被抓捕的准备,而她在设下将赵明义拉下水的局时,选中的那个真正来替自己「背黑锅」的人,其实是小姐。
想及此,郑怀的面上露出了难堪与愧疚,当即道:
“少爷,实在对不住。
“您本就与匡济会没有什么关系,又已经在组织转移的关键人物的事情上帮了很大的忙,我们都很感激。可不料如今,竟连把小姐也被牵扯了进来。但是少爷,我可以保证的,这绝非组织的命令,而是……”
傅斯乔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只问:
“阿怀,你是为了私人恩怨,才举起的枪吗?”
“当然不是!有识之士哪个瞧不出日国已是蠢蠢欲动,那群蛀虫却为了自己的私欲走私军械与药品,这与卖国有什么区别。”
“所以,既是关乎国家兴亡,匹夫皆应担责的事,你又怎么能讲完全与我无关呢?”
顿了一下,他又道:
“再者说,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卷进来的人是静筠,这句「对不起」和此后的一切解释,你都无需同我讲。”
前一句说得自是真心实意,可讲到后半句时,郑怀却瞧见傅斯乔眸底的黯影沉沉,裹着不明的情绪。他从十多岁起就跟在少爷身边做事,自然看得懂其中的「不快」,犹豫再三,还是说道:
“事情已经发生,我知道,自己道再多的歉也是无用。况且,以我素日对小姐的了解,一旦将事情的缘由说给她听,她便绝无可能需要我去请罪,但……”
话到此处,郑怀注意到原本沉在傅斯乔的眸底晦暗骤然涌了上来,在冷月的映衬下泛出森然的寒意,声音便卡在了嗓子里。
见他不再说话,傅斯乔便道:
“阿怀,我并不是一时兴起才选择帮助你们,既然已经承诺过,当然也不可能因为静筠的事就愤然到就此袖手旁观。所以,你此刻的那些忧虑,绝不会发生。”
短暂落针可闻的静默后,再开口时,傅斯乔语中的情绪终是起了显着的变化。
他说:
“但是,如果你现在非要让我说出「谅解」二字来安你的心,我也可以明确给你一个回复,「我做不到」。说白了,现在我此刻还能压住怒火,没有动手揍你一顿,已经是用尽了最后那点理智在反复劝说自己,「这事你不可能提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