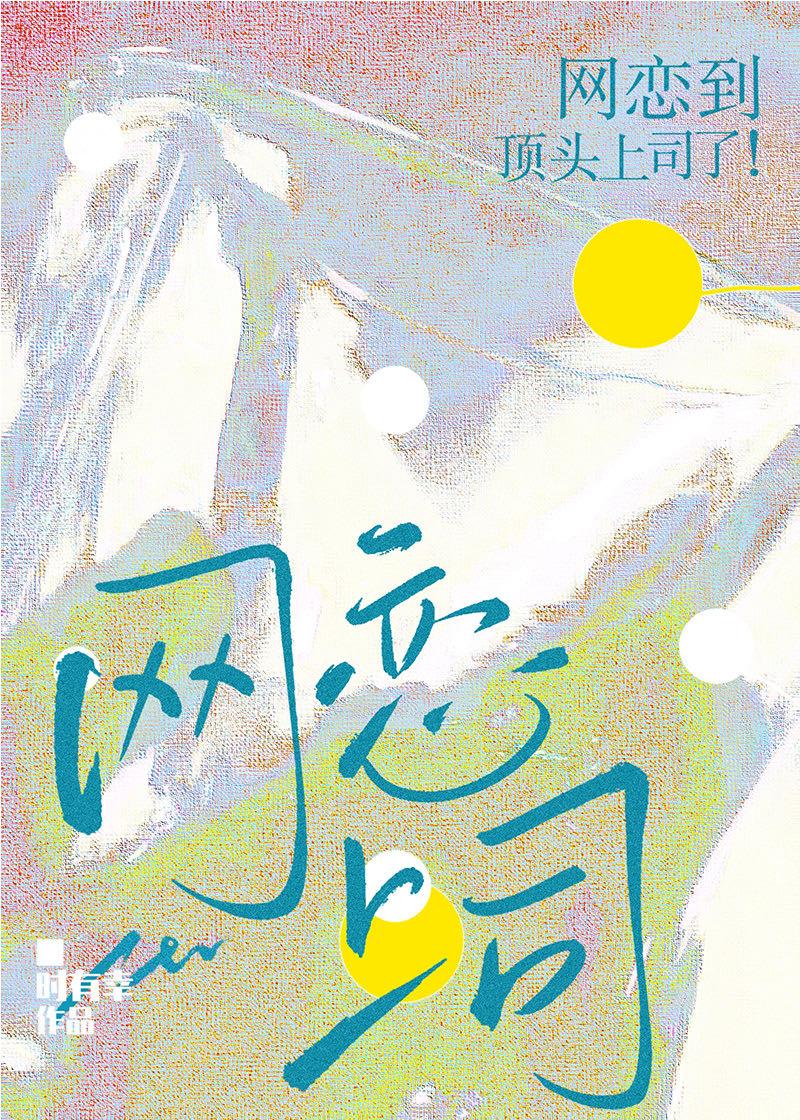69书吧>心机是什么意思女生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房间里,他把木棉放在床上,俯身查看他的手。
破皮的地方不再渗血,只是两只手红得厉害,仔细看时能发现片状的小红疹。
“又过敏了。”
涂抑把他的手放下去,“上次的药用完了吗?”
“没有。”
木棉说,“在药箱里面。”
涂抑起身拿了药箱进来,给木棉涂了层过敏药,又涂了层外伤药,然后又翻出纱布。
木棉低垂的眼睫动了动,问他:“干什么?”
涂抑说:“缠一下伤口。”
木棉掀起眼盖看他:“有必要吗?”
“有。”
涂抑笃定道,牵过他的手,将剪成小条的纱布分别绑在他受伤的指头上。
“好了。”
他看着木棉干爽白净的手,“明天应该就会好的。”
木棉反应冷淡,一声不吭地把手收回去,翻身想要往床里躺。涂抑抓住手臂把他扯回来。
“学长。”
他的瞳色比平时更深,这么定定地将人看住时,就觉得他奉献出了全部的专注,“你能告诉我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吗?”
木棉只是没有精神地说:“我好累,我想睡觉。”
说完,他再一次往床里软进去,涂抑这回放开他,不过还是坚持道:“那你躺着跟我讲好吗?”
木棉没答应,裹着被子翻身背对他,涂抑一点也不嫌麻烦地从床的这边换到那一边,蹲身与木棉平视着。
“学长?”
他的执着令人动容,木棉眨了几下眼睛,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丝丝可疑的水痕。随后,有些可怜地开了口:“我今天见了妈妈”
剩下的话不必再说,之前那通母子间的电话已经让涂抑察觉到他们严峻的亲子关系。
“没关系的。”
他轻轻帮木棉掖紧被子,又将他有些遮挡脸庞的头发挽到耳后。
木棉没有抵抗他这种过线的举止,甚至无意识地擦蹭了一下涂抑的手掌,显露出十分自然的亲昵。
他抬着眼皮将涂抑看住,眼睛很缓慢地眨动,“我好像总是做不好”
“不是的。”
涂抑说,“是阿姨对你太严苛了。”
木棉没有顺着他的观点讲话,他似乎真的累极了,眼皮缓缓掉落。创伤粉碎了他平日的冷淡和高傲,柔软得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脸颊往枕头里蹭了蹭,从喉咙里滚出一声轻哼之后他便逐渐沉入睡眠。
宁静的房间里,涂抑的呼吸声粗了又细,接着,他把手伸进被子,摸索到木棉的手掌。一半是纱布的粗糙感,一半是无暇而滑软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