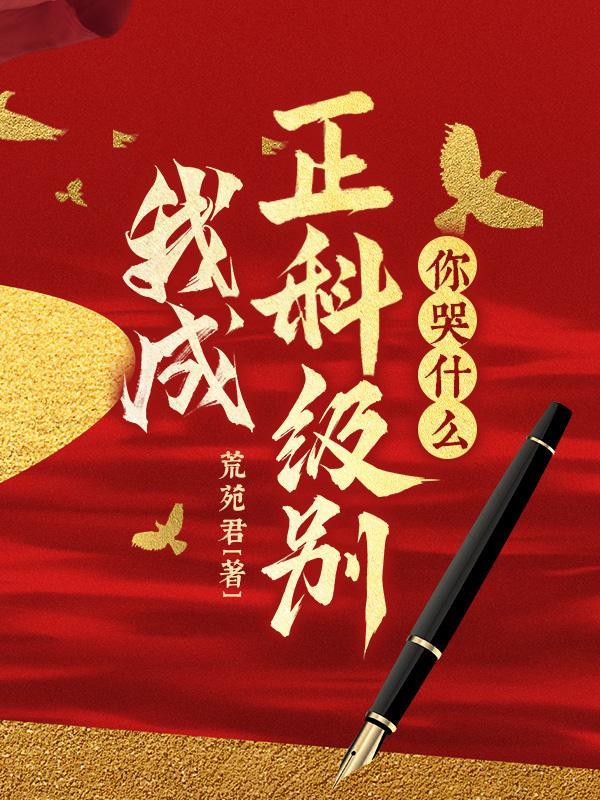69书吧>宠妃养成攻略by小蛮仙 > 第100页(第1页)
第100页(第1页)
皇帝坐上龙辇后却道,“今夜元宵,你不必当值,宫外不是有了家室么?出宫去与她团聚吧。”
司律向来是皇帝身边最受重视的宫人,按照萧叙的脾性,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大慈悲叫人回家与人团聚。
御前的其他宫人都醒了神,皇帝的这番话这对于司律而言,并非好征兆。
不过司律向来处变不惊,恭恭敬敬向皇帝行了一礼便坦然离开。在他看来皇帝生性孤傲,世人说他如何痴迷韦如是,也并不见得。任何一丝不在皇帝允许下的偕越都是死罪。而皇帝他习惯于驱赶走任何一个企图靠近他的人,将自己武装成刀枪不入无欲无求之人。对于这一点,司律也无可奈何。他作为奴,也只能是奴。
皇帝忽得从龙辇上下来,“朕独自一人走走。”
宫道两半皆是绮丽精巧的灯笼,放眼望去整个皇宫如梦如幻。萧叙反倒不喜,散了会儿步停下来,现自己不知不觉到了琴瑟殿,这四周一如往常般零星地挂着几盏琉璃宫灯。
守卫平日只放送饭的小宫人进去,万万没料到皇帝今夜亲自前来,立即打开大门。
琴瑟殿前庭的昏暗死寂令萧叙不自觉驻足,她禁足已经十多日,前些时日还算热闹的园子完全变了个样。紧闭的寝殿大门口放置着已经完全冷掉的饭菜。
萧叙推门而入,预备同他这位昔日的宠妃再周旋周旋,或者说训斥她几声叫她明白世道艰难。
寝殿之中也十分寂静,萧叙纡尊降贵亲手点了油灯,黑暗褪去,华贵陈设瞬间映入眼帘。
时语冰就在外室的木塌上昏睡着,被如此大的动静惊醒了。她额头冒着虚汗,浑身骨头如同被马车车轮碾过一般酸疼不已。
殿里有人,她心中闪过一丝欣喜,强撑着从床榻上坐起,映入眼帘的便是一身华衣、气质出尘的男人。
萧叙眼中眸光流转,一副来看好戏的架势,“今夜元宵节,这么早就安寝了?”
他的注意力不在于时语冰,而是漫不经心地欣赏着身边半身高的粉彩花卉花瓶。
老狐狸依旧是这幅讨人厌的模样。
时语冰靠到木塌上,伸手抓了抓乱成一团的丝。从前日夜里开始她便高烧不止,这会儿实在没精力与他周旋。
皇帝听她半天不出声,侧眸望过去。她看上去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有一丝狼狈,长而浓密的乌黑丝垂落下来,略显苍白的脸上并无一丝修饰,本该是一副惹人怜的模样,偏偏眼神中浮现着倔强。
“臣妾现在每日都早睡,陛下若无事就不要来扰人清梦。”
不知好歹。
如此伶牙俐齿叫人瞬间收起了那仅有的几分怜爱。
萧叙也没了逗弄她的心思,决意要走。殿外吹来一阵寒风,皇帝畏寒故而穿得厚实,这个时节他所在的宫殿大多燃着炭火,而此处除了昏暗之外更是冷如冰窖,她能睡着也真是匪夷所思。
见萧叙离开琴瑟殿的正殿,时语冰渐渐放松警惕,再一次为自己莫名的倔强和逞强而懊悔。
病了的人格外嗜睡,彻骨的寒意令她蜷缩起来,用厚实的被褥包裹住自己。闭上眼睛没多久,就觉得木塌边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时语冰骤然睁眸,见老狐狸去而复返,这会儿正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她。
未等她作何反应,藏在狐皮大氅下的手朝她伸来。时语冰本能地睁大双眸躲开。冰凉的指尖穿过额前的丝,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抚上了她的额头。
“你烧了。”
陈述语气里带着点儿幡然醒悟的意思。
“没有”
自己的故作坚强被人轻易拆穿,时语冰将他的手扯下,不论是语气还是神情都有些恼火,被泪水浸润的双眸瞪着对面的人。
皇帝将人从木塌里捞出来,掌心再次试探她的额头,她烧得浑身滚烫。
时语冰急于缩回被褥之中,偏偏那一双揪着她不依不饶,她呜咽着反抗。无力的动作被萧叙轻易化解。
他脱下身上白色狐皮大氅将她整个包裹,“朕去喊人。”
“走开。。。。。。”
她迷糊地咕哝了一声,扯下身上的狐裘。
下一瞬狐裘被重盖到她身上,“别再动了。”
萧叙的低声喝斥并不管用,但时语冰实在无力与他争执,再次躺回塌上陷入了昏睡。
再醒来时,已是半个时辰之后。
原本昏暗而冰冷的寝殿灯火通明,炭火盆里燃起的兽金炭彻底驱赶寒冷。她正躺在内室的床榻上,烟霞色床帐外隐约可见走动的人影,以及淡淡的苦药气味。
有人撩起了幕帘。
时语冰慌忙闭上眼睛,来人伸手触了触她的额头,袖口上熟悉的淡淡檀香气钻入鼻间。
萧叙摇了摇她的肩膀,时语冰继续装睡。片刻之后床帐之中又得了安宁,她才缓缓睁开双眸。
两边的床帐已经被彻底撩起。萧叙守株待兔,不动声色地立在边上,神色肃然,像是知道她在装睡。
“既生病了,为何不喊人?”
萧叙问道。一小宫人端着膳食站在皇帝身后。
时语冰心里对他可没有一丝感激,“臣妾罪人一个,病死也微不足道。”
皇帝并非心软之人,见她如此倔强,心里也烦闷极了。侧眸示意宫女退下,“既如此,今日也不必进膳。”
听闻这句话,时语冰掀过被褥翻身面朝内侧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