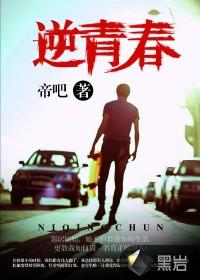69书吧>七海博物志免费阅读最新版本 > 第77章(第1页)
第77章(第1页)
>
“这样鲜艳颜色的动物,一定有毒,就和蕈菇是一样的。”
彩岳大娘点点头:“这种蛙的身上有剧毒,若是顺着血液进入到人的身体里,一天之内就会麻痹而亡。听说在大荒的部落里,会把它们的毒涂在箭镞上。”
越翎听了,一阵害怕,赶紧用积水凤梨的叶片把它赶走了。
就这样几日,终于抵达赤水河畔的桑榕寨。
从桑榕寨往树林深处再走个一两天左右,就能抵达其中的蝴蝶谷。
彩岳大娘把小舟系在村寨门口。
众人下了船,走到桑榕寨里。这里的房屋是比千水寨更高的吊脚楼,只有寥寥十几户,散落在遮天蔽日的桑榕树间。
岑雪鸿环顾一圈,桑榕树特有的板状根巨大而虬结,其上附生着密密麻麻的蕨草,裂开的每一瓣叶片都在尽力扩大自己的面积,争夺从桑榕树间漏下的一丝阳光。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一个村民模样的人问。
“我们要去蝴蝶谷。”
彩岳大娘说。
“哪有这时候进蝴蝶谷的?”
那村民听了便惊讶。
彩岳大娘拿了几两碎银给他,让他安排住处,那村民得了钱也就不说话了,把他们往自己家引。途中彩岳大娘和他交谈了几句,知道了他是村长的儿子,叫做阿锟。
岑雪鸿与越翎跟着走在他们身后。
不知道为什么,岑雪鸿自从踏入桑榕寨里,心里就一直感到很慌。
她转头去看越翎,他没说话,剑眉却也拧在一起,面色凝重地望着被桑榕树遮蔽的天。
岑雪鸿忽然发现,连着两个月的奔波以来,越翎似乎长大了。
从前那恣意之中带着一丝小男孩儿的幼稚,而现在,少年气褪去了一些,增了几分成熟,令他看起来介于少年人与男人之间,蓬勃生长,锋芒却向内收敛。
天阴沉沉的。
走了几步,岑雪鸿反应过来了,是因为空气变得极为凝稠而厚重,甚至呼吸有些都不畅,才会有与心慌相似的感受。
要下雨了。
这场雨绝对与他们一直以来所遇到的不同。
这是一场暴雨前的征兆。
岑雪鸿再去看越翎和彩岳大娘的表情,心里明白,他们都意识到了,只是忍着没有对她说。
跟着阿锟踏入他家的一瞬间,几滴温热的液体,落在岑雪鸿的额头上,令她想起前几天的夜里,越翎与她额头相抵时的温度。
一抹赤金色极速坠落。
岑雪鸿摸了摸额头,那不是雨水。
指尖上,沾着新鲜的血迹。
与此同时,越翎伸出手,接住了那一抹赤金色。
金练鹊躺在他的掌心里,尾羽凌乱,疲惫不堪,奄奄一息。
眼角和嘴角流出的血,淌了越翎满手。
“太白!”
越翎喊。
这样只能短途飞行的小雀,是如何飞过几百里,从分野城找到这大荒郡的?
它像是拼着死前的最后一口气,坠落在了越翎的掌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