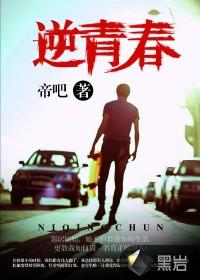69书吧>窃唐僧袈裟的有红孩儿吗 > 第058节 秦门藏玄机(第1页)
第058节 秦门藏玄机(第1页)
?从齐郡东门穿行到西门,衢道间车水马龙,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熙来攘往,路两边酒肆、当铺、镖局、印染等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打铁的、卖艺的、耍猴的、吆喝耗子药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端的是一派热闹盛世之景。
一路风景无限,李罗二人无心留恋,在拥挤的人群中躲闪穿梭,车上的石头那么重,生怕一不小心碰伤了无辜百姓。短短的几里路,他们两人累得满头大汗。
等赶到西门外的时候,天色已过午时,在罗士信的指点下,二人急不可耐赶到秦家铁铺前。这里挤满了打制铁器的普通百姓,铁铺内传出来刺耳的打铁声。
挤进铺后,李栋现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人身高七尺,比自己年龄稍大,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脸色被炽热的火光映照通红,额头宽宽,鼻如悬胆,面部骨格清奇,显得刚毅有力,棱角分明。
两撇英雄眉横插入鬓,看上去英武非凡,特别他那双眼睛,紧盯手中的活计,将手中铁锤稳键击打在烧得通红的铁模上面,点点火星飞溅,他丝毫不受影响,哪怕身边的人来来往往语声喧闹也浑然不觉,依然将手里的铁块一下又一下照打不误。
另一人的年龄约四十岁左右,像是少年郎的父亲。他拿一把鸡蛋大小的锤子,“叮”
的一声轻轻敲打铁块间。年轻人手中的大锤随后也“当”
的一声,毫无偏差的打在相同的地方。
他们二人你来我往,你往我来,只顾埋头打铁。中年人偶尔抬头回复来人的问话,有时头也不抬,让他们自己挑选,挑好后把钱或绢帛放在一处。至于他们是否放了,却不去过问。
打了一会儿,铁块由红渐黑,由软渐硬,中年人将铁块放回炉内继续锻烧。并蹲下添些柴火,忽嗒忽嗒拉几下风箱,炉内的火更加旺盛起来。
这个时候,少年郎将浸泡在水里的,已经初具模样的粗胚,放在铁砧上轻轻敲打,把不满意的地方再仔细雕磨,片刻间那模具就更像模像样了。
站在铺前看了好长一段时间,李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用眼睛将铁铺内的一事一物看了个遍,生怕一说话就打破了父子二人温馨有序的节奏。
门前的人太多了,这批人前脚刚刚离开,那批人接着又挤过来。挑到满意的东西,留下钱物转身就走。
李栋又挤回去了,与罗士信找个饭馆,要了两碗面片儿,先填饱肚皮再说。
罗士信饭量大,一碗不够吃,只得再叫两碗,由着他的性子吃个够。
一边吃,罗士信一边问:“干吗不告诉他们,我们是来打铁的?”
李栋微微仰头,望着房顶出一会儿神,才轻声说道:“对于手艺高的人,我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过去丢了钱转身就走。我们要和他们多谈谈,把我们的想法啊要求啊一一告诉他们。你也见到了,他们很忙,还不方便与他们仔细谈兵器的事。”
“那什么时间最合适?”
夹了满满的一筷子面片,罗士信填进嘴里,一边吃一边含混不清的问道。
李栋道:“等……等人少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再去秦家铁铺。”
“那就坏菜了。秦琼一天只打十把铁器,多一件也不肯打。现在已过午时,恐怕没戏了。”
说话间第一碗面被吃得净光,罗士信捧起第三碗面,稀哩呼噜吃得有滋有味。
“……”
一天只打十把铁器?李栋一听罗士信的话当即没词了。有这条件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现在人都站在秦家铁铺前了,才支支吾吾提出来?尼玛坑爹啊!
今天不打兵器,这石头死沉放在哪里?一天还好凑和,明天还排不上号,没有轮到订制的机会,又怎么办?
难不成天天带着这东西满大街跑?
李栋有些焦急,双手对搓,脑袋飞快想着方法,怎么做才能突破秦琼的限制。
难题抛给李栋了,罗士信捧着第三碗面片儿,只负责把嘴皮子巴咂得山响。
他吃光面片儿后,李栋付了账,拉着他的手朝外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