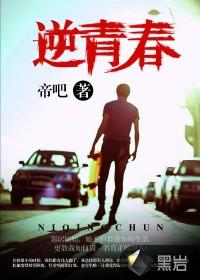69书吧>森茉莉养鱼手札绮罗春 > 第55章(第1页)
第55章(第1页)
“你做这么过分的事,就不怕有一天别人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你?”
太宰治微笑着:“听你这么说,我简直有点期待了。”
车,直升机,然后步行,茉莉都搞不清自己还在不在横滨了。当到了这被守卫严密看管,光看就知道不是好地方的军事设施,压抑的不详预感逐渐变得浓重。
常人想要出入应该很难,但太宰治简直是这世上最机灵的潜入者,这里的守卫,布局,甚至密码门的密码,他都好似提前知道并且刻入脑海,就算带着茉莉也称得上畅通无阻。
茉莉面无表情,不想说话也提不起劲问他什么,她总觉得能隐隐约约听到些什么,又觉得脑袋在隐隐作痛,不能确定那是不是耳鸣。
直到最后那个房间的门在她面前打开,呈现在她面前的景像和那简直不像人类可以做到的痛苦嘶吼,才终于把可怕的预感化做更恐怖的事实。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反应过来时,她已经离被带刺铁线粗暴地吊在墙壁上的中原中也很近了,耳与脑都被那痛苦的嘶吼填满,无法再把心神分给其他任何事物。
中也的身体被两根木桩贯穿,那上面有电流缭绕的闪光滋鸣,他颤抖战栗,为这人类……生灵不该承重的苦痛。
为什么要这么对中也?
茉莉茫然不解,她不明白,如此般对待中也的人,究竟是打算从这个已经承受了太多迷茫和苦痛的少年身上,再压榨掠夺些什么!
到底是什么,竟然值得他承受这样的苦痛和折磨?
她又怔怔地向前近一步,从心脏的最深处,或者是更深邃的地方,随着血液奔流,有什么幽深可怖的东西逐渐苏醒、蔓延。
这是无法阻挡的,最冰冷最黑暗的潮涌,在她那幼小孱弱的身体里成形,侵蚀,蔓延。
心理所当然地驾驭形体,无坚不摧之刃是个谬论,本不该诞生,存在就意味着可以撕碎一切阻碍。
它的声音,就算法则也非聆听不可,它想作为人类诞生,那就可以诞生,限制再多,被割裂分开的力量,一旦它想,就会撕裂一切阻碍,顺从心的意志,完整地降临于世。
什么事是可以做的?
什么事是不能做的?
人类制定的规则,说到底是群必须依赖彼此的家伙用来约束彼此,以不能互相伤害为基础,互相帮助的条约。
这使散沙般的人类成为群体,为到渺小个人做不到的事,本质上集中并延展了人类的力量。
如果有一种存在,生来就能摧毁一切,如同灾难,仿佛毁灭本身。
那么规定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是最愚蠢无聊的事了,毁灭就是它天生的权柄,谁也不能宣判它有罪。
茉莉怔怔地又向前一步,伸出手试图碰一碰她所珍视,正被蛮不讲理,用最粗暴方式折磨对待的存在。
到底是怎样的意志力和执着呢?竟让中原中也在这般非人的痛苦折磨下也重新凝聚意志。
他那没有焦距的瞳孔中,逐渐走近的小小身影,唤醒了他的意志。
事实上,中原中也无法分辨这是真实还是幻觉。
就算是再微小的可能,也无法置之不理,他他颤抖着嘴唇,细如蚊吶,祈求似地说:“快逃,快逃啊……茉莉!”
如同被惊醒,就像被什么砸中脑袋,茉莉猛地一震,才终于看清自己面前的是什么。
在她面前的是——伤痕累累,不堪重负,就快支离破碎,也不知被什么样的意志支撑,还在苦苦挣扎,不肯放弃的中原中也啊!
他还没有放弃,他还在挣扎!就算被这样折磨,就算这么痛苦,他也依旧想活下去啊!
“啊!”
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像是意识到自己面前正发生这世间最可怕的事,像只下意识躲避利箭的鹿一般转身逃了。
中原中也看着她的身影消失,这才安心地,痛苦地呼出口气来。
逃出那个房间,就这么简单的举动,花光了茉莉所有的气力,她脚下一软,摔到了地上。
就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能可怜地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太宰治走到她身前蹲下,细细打量她的神情,问:“你还好吗?”
茉莉虚弱地看着他,颤抖着嘴唇艰难道:“你,快去救,中也……”
“不用担心,已经有人去救他了。”
然而他并不把心神分给其他,只专注地看着茉莉。
太宰治伸手捧起她的脸,那小心而珍视的模样,就像在检查名贵易碎的瓷器上是否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
茉莉确定他说的是真的,但也无法因此感到释然或安心,更深更重的无力感从心底泛起,让面前的景象蒙上层灰般变得不真切了。
“你想看中也痛苦。”
这是个阵述句。
太宰治微笑,鸢色的眼中一丝光亮也透不出来。
“我想看中也作为人类痛苦,他想确定自己的存在……作为人类存在,我虽然不理解他的执着,但我想完成他的心愿。”
原来他在意并且倾听着中原中也的心生,他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完成它。
这家伙确实有哪里坏掉了,他会用最残酷冷血的方式达成所想,说不定比魏尔伦更不像人。
“你不觉得吗,痛苦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几乎可以说是某种标志,我想送给中也的那种痛苦,就像婴儿诞生于世间,啼哭着接受第一口空气,那样泌入心脾的痛楚,恰恰是活着的证据。”
是吗?中也需要的是这个?
茉莉无法确定,不能理解。她笃定地说:“你想看我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