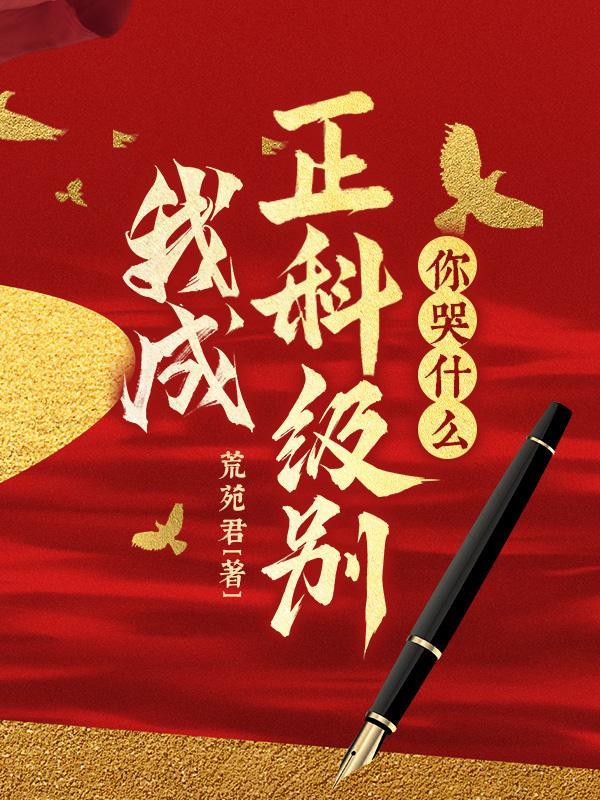69书吧>七爷为什么叫七爷 > 第56章(第1页)
第56章(第1页)
原来二人在唱一出戏,谢必安无动于衷,当个冷面的过客,阿箩先恼后羞,最后不胜羞涩,扭捏着身子飘回谢府了:“呜呜,八爷也坏。”
“别闹她了。”
等阿箩离开,谢必安才出声岔断二狗子和范无咎的戏。
“这不是在帮小白你试探吗?”
范无咎转着把洒金黑扇飘到谢必安身边,“反正你也不舍得她走了,总不能让她在地府里永远当个小跟班吧。”
说着,他抓住一根出墙来凑趣的柳枝,再道:“托这多嘴柳树的福,我们知道你俩如今不是皮里膜外的关系了,索性就成亲吧,这地府还从没办过热闹的喜事儿,我想到时候应当热闹非常。”
谢必安没想过要和阿箩成亲,他觉得保持这样的相处没什么不妥。但他与阿箩相处了几百年,感情愈发不寻常,在做了沾皮的事后情也渐深,成亲也没有不妥之处。
范无咎的力气大,柳树在哪儿疼得哇哇连珠箭叫七爷救命,并用其余出墙来的柳枝绕住谢比安的手臂。
柳树再多嘴也是自己种的柳树,谢必安瞟了一眼范无咎,示意他放手:“放开它吧,它闹起来比阿箩还吵。”
“我知道了,小白看似冷淡冷清,其实心里火热,就是喜欢吵闹的玩意儿。”
范无咎松开柳枝,啧啧嘴,带着二狗子飘然远去。
谢必安懒去反驳一二,安慰了几句正在吃屈流泪的柳树,就去寻阿箩了。
阿箩趴在横梁上不敢下来见人,谢必安在底下仰头叫她:“害羞了?”
“有点。”
阿箩轻点头,这一点,头又掉了,身体叵耐从横梁上下来。
接好头,谢必安继续方才的话题:“那你觉得八爷说的那件事如何?”
阿箩知道是什么事,一双眼不定转,装傻来应对:“什么事?”
“就是火热热的喜事。”
谢必安直言,“阿箩,你想和七爷成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