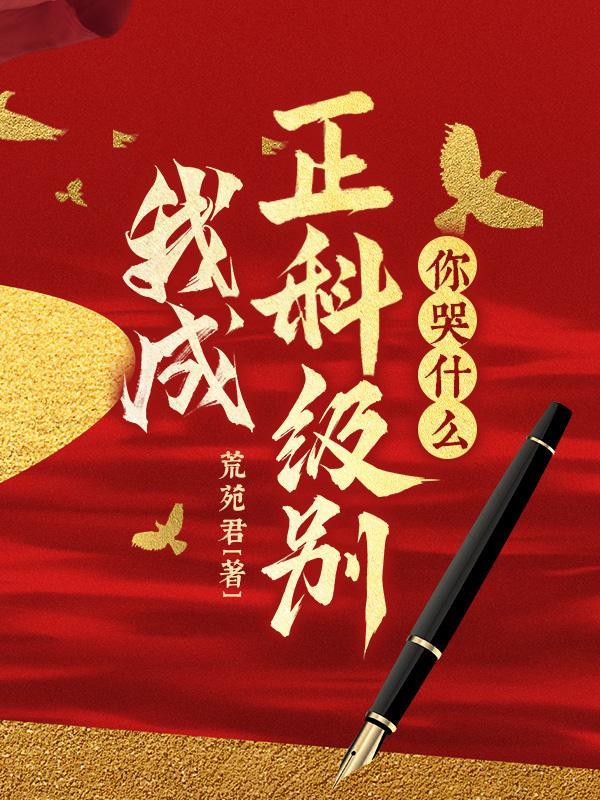69书吧>锦衣褪尽晋江 > 第38节(第1页)
第38节(第1页)
此人身上的棉袄层层叠叠打着补丁,两袖口和膝间因着日常劳作而沾染了大片污渍,经由一冬已成了黑亮黑亮的模样。
便听这老伯愁眉苦脸道:“大人啊,这不还没到农忙,小老儿就跟着我们村的王大冯柱子他们上山去看看能不能捡点野物儿,早知道这么着,哪敢跟他们凑这个热闹啊。”
蒲风点了点头。
老伯便咽了口唾沫继续道:“这大正月里的,谁知道刚绕到后山阴背面就瞅见道边雪堆里露出来一只鞋,瞅着还挺好的,王大还想捡来呢,哎呦……那鞋还套在死人脚上喽。”
“雪堆里?”
“绝不骗您啊,大人。阳面上的雪是都化了,那阴背面的雪堆能搁到清明都化不完。我们一看是死人哪敢跑了不管,一合计就抬着脑袋跟腿送衙门来了。这人也不知道冻多久了,梆硬梆硬,跟根儿木头桩子似的。”
蒲风颔首,“还有呢?”
“剩下的真就不知道了,大人。要是没事儿,小老儿能不能撤了,大正月碰上这事儿是真晦气。”
蒲风回头扫了一眼尸首,招来两个衙役道:“你们俩,好生将老伯送回家去,顺带去走访了一同上山的王大等人。”
待那老伯千恩万谢地走了,蒲风才一同蹲在尸首边上,垂眸低声道:“当务之急是先断出来死者的身份,你看他这身衣服还是绸缎的料子,想来并非山脚的穷苦人家出身,可大冬天上山要干什么去?”
刘仵作一件一件整理着死者的衣物,顺带将细小的杂物整齐摆放在一旁的漆盘里,并没有答话。
蒲风一面看着死者一面扫视着那堆配饰钱袋之类,目光落在了那个香囊上,青绿色的缎面上绣着一对鸳鸯。
蒲风将那香囊取过来,解开中间的缩口,只看到香囊里面填充的是许多药粉,现在闻起来还是有些冲鼻的辛香。
她回过神来便见到刘仵作已经开始细致地每一寸检看着死者周身。蒲风莫名地想到了李归尘,想到了他清冷而又专注的眸子,还有那双虽不甚修长却骨节分明有致的手。
他会忽然抬眸凝望着自己,四目相对间,蒲风常会有一种被审视的错觉。
“说说你都看出什么了。”
这是他常说的话。
蒲风忽然微微挑了嘴角,继而正色盯着尸首道:“死者面容安详,体态自然,手指脚趾都有青紫的冻伤,尸斑又这么鲜艳,大致应该是冻死的。”
刘仙颇为惊奇地抬头望了蒲风一眼,点头道:“大人果然好眼力。依小人验尸八年的经验来看,死者的确是冻死的。您看看此处也有挛缩,嗯,必然是冻死的不会错了。”
蒲风垂着眼皮草草扫了一眼,红着脸打着哈哈道:“是,是……”
刘仵作笑了笑,摇摇头又将尸首翻了个身。
蒲风只见大片鲜红如血的尸斑弥漫在死者的背上、臀后、两股,再看风干的程度,推测这尸首已死了十日以上。
她又托起死者的手来打算仔细看看他冻伤的手指,便意外见到死者右手中指指甲左侧、食指第一节左侧一并大拇指指腹都生了一层茧子,连指纹几乎都要磨没了。
这一点就有些意思了,像是农夫或是柴夫日常劳作,掌心一般会磨出厚茧来;而书生一并书吏之类常年握笔,食指可能会有些微微变形且生出薄茧;然而这指腹生茧又会是因何呢?
蒲风百思不得其解,便捏着手里的笔模仿了起来。这种动作看着就像是一种怪异的写字姿势。
“蒲大人你干什么呢?”
刘仵作好奇道。
“没事没事。”
她一手按着眉头,许是蹲得有些太久了,自后腰的肌理深处不断传来一袭一袭的隐痛。蒲风只好扶着身边的柱子慢慢站起身来,即便如此她还是眼前一黑,心里更是扑腾得厉害,缓了好久才慢慢好些。
蒲风忽然想起来前日裴大夫说的那些话,他还叮嘱自己每隔三日便要去扎一次针……一次针……针!
如果她手里捏的不是一只笔而是一根纤细毫针的话,一切都能解释的通了!
死者乃是位郎中,他手上的薄茧正是经年累月给病患扎针所致。蒲风也知道那后山上虽人烟稀少倒也的确有几户人家居住。
夜里出诊迷路不幸冻死路旁?若不是那本《业镜台》本是她自己亲笔所写,蒲风也几乎要将这案子视为一起普通的意外案件。
《寒症》一文中“刘神医”
的下场便是如此冻死在路旁了。
她的面色忽然就阴沉了下来,此前的剥皮案将凶手指向了这顺天府衙门之中。若这冻尸案的确和《业镜台》有关,那以此杀人为乐的凶手少不得要伺在暗处偷窥,如此一来更能满足他疯狂而又扭曲的欲望。
故而,蒲风虽然看出了死者并非是正常死亡,却半个字也没有多说,只是跟后来赶到的何捕头轻描淡写嘱咐了几句尽快找到死者家人,在此之前保存好尸首之类,甚至连验尸单子都没多看一眼。
趁着丁霖和他手下都没注意,蒲风偷偷潜入了案宗室,翻了许久终于找出来了一份顺天府衙门的供职册。这里面详细记载了顺天府衙门上下各个职位的人员姓名及户籍。
蒲风左顾右盼着压住了心中的狂跳,她本想将册子塞到袖子里,又怕一会让丁霖看出破绽来,想了想只好将它自领口垫到了背后。因着这衣服本就宽大,腰带勒得紧些是万万不会被人看出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