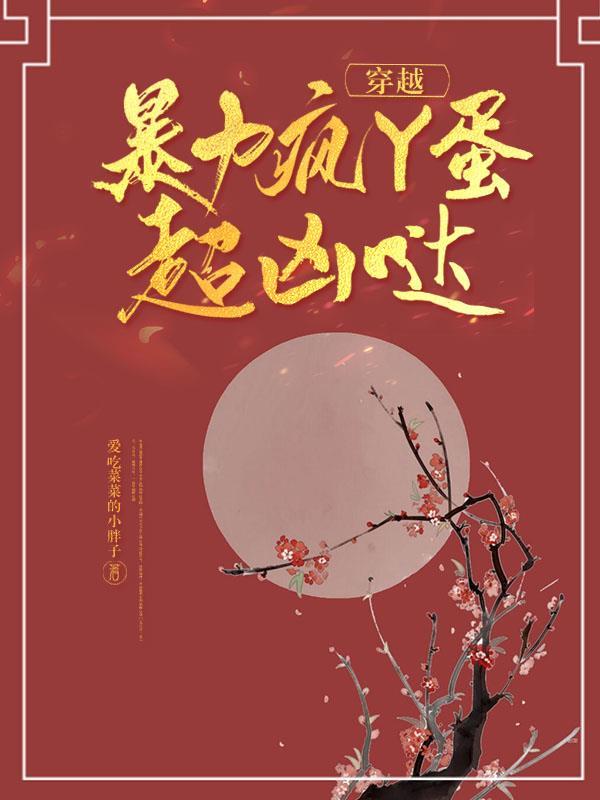69书吧>她算什么男人无防盗章 > 第十二章 白银千两(第1页)
第十二章 白银千两(第1页)
第二天梁善如和周慎起了大早。
晨间雾气散去,天果然放晴。
冬日里云层总是厚重,金盘羞怯藏于其后,只能勉强看出丝丝缕缕的光。
檐下冰凌有了消融痕迹,滴答水声不时能传入耳中。
从周慎的别院到侯府不过一刻而已。
长乐侯府今天似乎极热闹,门上当值的小厮从天刚擦亮就忙活起来,这会儿见周家马车停在府门外,掖着手下台阶迎上来。
周慎先行一步下了车,多余的眼神没分出去半点,递了手臂接梁善如。
她一边下车,见了那圆脸的小厮,随口问道:“府上来了很多人吧?”
小厮颔首说是:“一早就忙活起来,奴才听里面的人说好茶好点心的端到前厅,从没见夫人如此和颜悦色的。”
周氏就是这样的人。
侯府的穷亲戚实在不少,以前人家上门来周氏总不耐烦,恨不得干脆把人拦在门外不见,因为知道那些人是来打秋风要银子,怎么会有好脸色?
周慎闻言也不阴不阳哼了声,梁善如反而平静如常。
等真正进了府中入正厅,把一屋子人看清楚,梁善如才啧了声。
她那一声不算低,屋中众人听得真切,长乐侯面上挂不住,要不是忌惮周慎,此刻又要骂人了。
左右已经撕破了脸,周氏不愿意平白给梁善如打嘴,坐在那儿没动,只是唉声叹气叫善如:“你说要脱离梁家,今天族老们都在,昨日你是如何在你大伯和我面前耀武扬威,眼下再说一遍吧。”
她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话音才落下,垂首擦泪,抽抽搭搭的声音不轻不重,却正好能送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梁善如歪头看她:“侯夫人委屈什么呢?这些年您以教养我为名,把持我阿娘留下的陪嫁,扣着我爹爹多年来所得赏赐,更有甚者连我阿娘陪嫁的铺面田庄不也是你在料理?
这些年所得几何,我一概不知,你和梁宝祺母女一年四季裁制新衣,置办头面,是哪里来的银子?
怎么你们得了诸多好处,现在反而成了受委屈的?”
周氏的抽噎声一僵。
她还没开口,坐在她左手边的白发老者先沉声斥道:“你还没脱梁氏籍,此刻仍是梁氏女,就敢这样跟长辈说话,真是无礼!
你爹娘从前就是这样教你规矩的吗?”
梁善如眯了眼就要说话,周慎不动声色把她往身后护了一把:“善如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她今岁十六,按照长乐侯夫妇所说,这些年他们夫妇悉心教导,无不用心,如今善如没规矩,自然就不是梁兄夫妇之过。”
那老者横过来一眼:“周节度使位高权重,也不至于别人家事都要横插一脚把?
听说昨天还在侯府大打出手伤了人,我说这丫头过去几年装得安静柔顺,怎么突然这样,原来是有周节度使撑腰。”
他突然站起身:“要不然周节度使也给老朽来上一拳,最好一拳打死我,否则也堵不住我的嘴!”
人家说秀才遇上兵才有理说不清,这会儿却反过来。
周慎一个领兵的,遇见这么个不要脸的老泼皮,弄得他真想把人打死算完。
![女道君[古穿今]](/img/1495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