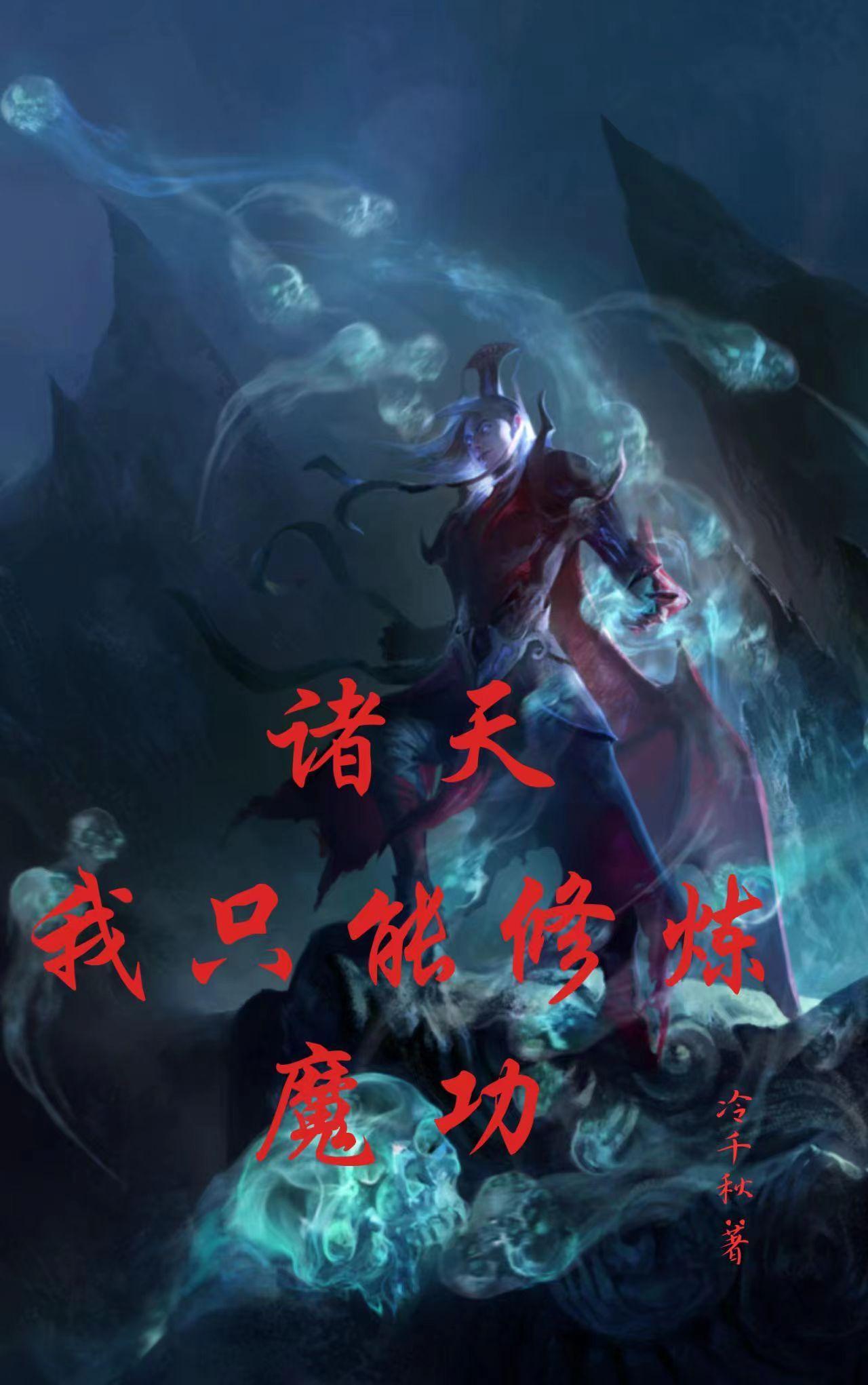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桃花妆典故 > 第090章 公主 胡扯本宫才不会心悦你(第2页)
第090章 公主 胡扯本宫才不会心悦你(第2页)
雒妃眯了眯桃花眼,上挑的眼尾不自觉带出勾人的艳色来,她目光审视地在秦寿脸上一扫,冷笑道,“驸马真是好大的脸面。”
秦寿半点都不恼,“脸大不大,我是不晓得,可我晓得,定然是俊的,不然如何能入蜜蜜的眼,上蜜蜜的心。”
雒妃总觉得这样的秦寿有古怪,瞧瞧这一言一语,哪里像是他这样的人能说出来的。
他不该是冷着张脸,略带恼怒地盯着她,再放些狠话之流?
似乎瞧出雒妃所想,秦寿轻描淡写地道,“蜜蜜不必疑惑,廊城那一遭,历经生死,九州也算想明白了,既然你我夫妻已是铁定的事实,且九州是尚的公主,这辈子不能再有侍妾,不为秦家子嗣后代着想,我也该多思量自个的日子,与蜜蜜怨偶成仇是过下去,琴瑟和鸣也是过的,是以……”
他顿了顿,烟色凤眼深邃如墨地看着她,“我为何要与自个过不去。”
这话让雒妃忽的就想起上辈子来,好似也在廊城事了之后,秦寿确实是与她关系有所缓和,待她好了脸色,也时常会送她一些小玩意,后来两人渐至蜜里调油,就那么好上了一两年光景。
可而今,那些再是美好的回忆,在雒妃看来,不过是秦寿扯的遮羞布罢了,为了日后的翻脸无情,也为了夺她息氏江山!
她冷笑,心头冰寒一片,“哼,驸马这会不怪本宫出身帝王家,日后面临抉择是做秦息氏还是雒妃公主了?”
原封不动的话,她还给他!
秦寿轻轻皱眉,又很快舒展开,他摇头微叹道,“世事如此,出身立场你我本是无法选择。”
末了,他又意味深长地道了句,“且还未到那等地步,蜜蜜怎知世事无变化?”
拥有前生记忆的雒妃,显然是不信他这话的。
秦寿定定瞧着她,那一线丹朱色陷进眉心皱痕里,颜色深而细,“蜜蜜……”
雒妃腾的起身,居高临下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来人,驸马用膳好了,务必要将驸马安然送到鸿鹄阁。”
话音方落,她一拂袖,转身离开。
秦寿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起开,曳地长裙在灯影下蔓延开深深浅浅的暗影,一如她现在的心思,也是不好猜。
凤眼之中晦色难辨,他微微垂眸,又重新执起象牙箸,慢条斯理的用起变凉的膳来。
却说雒妃回房,她才想起今个晚上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反倒说了一堆,她恼怒起秦寿来,只恨不得捆个秦寿小人用针扎他!
不过她还是将首阳唤来,并将今日秦勉要利用安家往城里塞人的事叮嘱了,让去一趟鸿鹄阁告之秦寿知晓。
首阳得令,匆匆去办了。
雒妃这才心有疲惫地躺回榻上,一闭上眼,她就想起从前来。
对她好过的秦寿,对她坏过的秦寿,以及最后杀她的秦寿……
诸多纷杂的记忆,让她眉心抽疼,她根本分辨不出哪一个秦寿才是真实的,亦或不管对她好坏的秦寿都是假的,唯有那个杀她的才是真实的。
因着记忆而带来身体上的反应,雒妃闭眼捂着胸口,就觉疼的慌,她蜷缩起身子,企图获得一点慰藉,然她如何也忘不掉秦寿那时的神色,淡漠无情,眸色深不见底,薄唇抿成直线。
她并未从他脸上看出半分的犹豫和难过,与她纠葛了十年的驸马,竟不会为她的生死而动容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