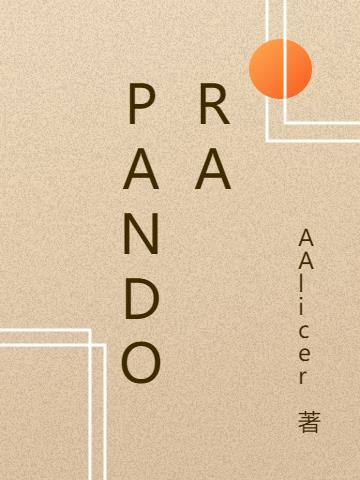69书吧>鱼目混珠是什么生肖? > 第45章(第3页)
第45章(第3页)
开春新委派了两个按察使监督进程,终于在夏初迎来开垦的荒地长出稻谷的好消息。
新帝大悦,一道几千里加急的折子褒奖当地官员,临退朝前还不忘叮嘱百官这才是他们应该办的实事。
一个半时辰后,走出大殿的百官长吁一口气,既感慨新帝精于政绩,又对新帝无意后宫纳新感到无可奈何,堂堂一个皇帝,整个后宫空无一人,史无前例。
傅至景才不管他们怎么想——他仍是这样称呼自己,好似要借此来留住些什么。
从早到晚,他都在光庆殿里处理政事,一天要批上百道折子,上至堤坝水库监修等大事,下至某地今年产出的橘子不够甜、哪两个县官产生口角告到中央这等小事,他通通都要自己过目。
如此的励精图治,朝中事无巨细皆逃不过新帝的眼睛。
他刚上位时很是大动干戈,有些脖子硬的不当回事,一条条罪证罗列出来,管你在前朝有多少丰功伟绩,管你做了多大的官,铁证摆在面前,一个个卸官逮了下狱,再替上亲手提携的新官,没个半年,朝廷官职布局就大换血,处处都是新帝的人。
新帝把“杀一儆百”
这四个字运用得炉火纯青,先抓个典型处死,再放话若有同罪者要么自从轻落,要么把捅出的篓子打好补丁既往不咎。
到了现在,无人再敢阳奉阴违,整个衡国上下一派清明。
给最后一道折子盖上朱印已近深夜。
侯在一旁的大内监只见新帝抽出川西递上来的折子看了又看,不知道回忆起些什么,唇角微微翘起,难得地存了点笑意,但很快的,这点笑容就如同燃尽的油灯倏地灭去。
傅至景揉揉胀的眉心,摆驾去寝宫太和殿。
銮驾慢悠悠地在宫道里前行,前后各随行四个御前侍卫,大内监福广微胖,垂跟在一旁,走了段路就气喘。
傅至景一到太和殿,伺候的宫人就乌泱泱跪了一地,他目不斜视地走进正殿,里头已提前点上了清幽的安神香。
宫人端上铜盆,他洗过手,福广跪下来给他宽衣,脱得剩下寝袍,他随口说了句,“圆机该送香来了吧。”
圆机是皇家寺庙里的一个耄耋高僧,去年的雪夜新帝命他来宫中做法事,二人曾有过一番交谈,此后的每月圆机都会差人送香到宫中,以及一句“陛下可有如愿见到梦中人”
的问候。
傅至景仍是相同的回应,“未曾。”
香料越烧越浓,纵能助他一时入眠,却始终未能解他心中之苦。
他挥挥手,福广会意地推到外殿守夜,依稀还能闻见从内殿里传出来的香气。
不到三个时辰,天还没亮,傅至景就醒了,摸一下空荡荡的身侧,久久没有动弹。
五年了,近两千个日夜,孟渔,你还是不肯到梦里见我一面吗?
“什么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我听不懂。”
“谁要跟你在梦里相见,如果哪天你不要我了,我绝对不会在梦里见你……”
当年在川西孟渔意气之下说出的话语竟成了真,无论他如何相思入骨,孟渔都不曾来看他一眼。
他宁愿孟渔恨他,哪怕化作厉鬼来向他索命也好,可偏偏应了那句“若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留在阳间的人使劲浑身解数抓不住游荡的魂。
傅至景不信神佛,却怕含冤而去的孟渔不得安息,请了得道高僧为之度。
圆机要助孟渔往生,被他厉声驳回了,他是那样的自私,要孟渔再在人间徘徊,等他百年后与他一起走奈何桥,再转世做一对羡煞旁人的好鸳鸯。
不必太久,只要再十年,他会亲自去跟孟渔赔罪。
傅至景甚至命令圆机设法抓了孟渔的魂魄,日夜栓在他身边,别说这是无稽之谈,就是真能办到,也是太损阴德的造孽之事,圆机畏惧君威,不得已打了诳语,道他执意如此恐吓得孟渔魂飞魄散他才不得已作罢。
安神香既助他入眠,又借着香味打通阴阳两道,让旧人进梦幽会。
可直至今日,香料每夜焚烧,他梦里始终是白茫茫的一片虚无。
香料快燃到了底,气味逐渐淡去,若孟渔这时想来看他岂不是被耽误了?
傅至景近乎是气急败坏低重重拍了下床榻,喊来福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