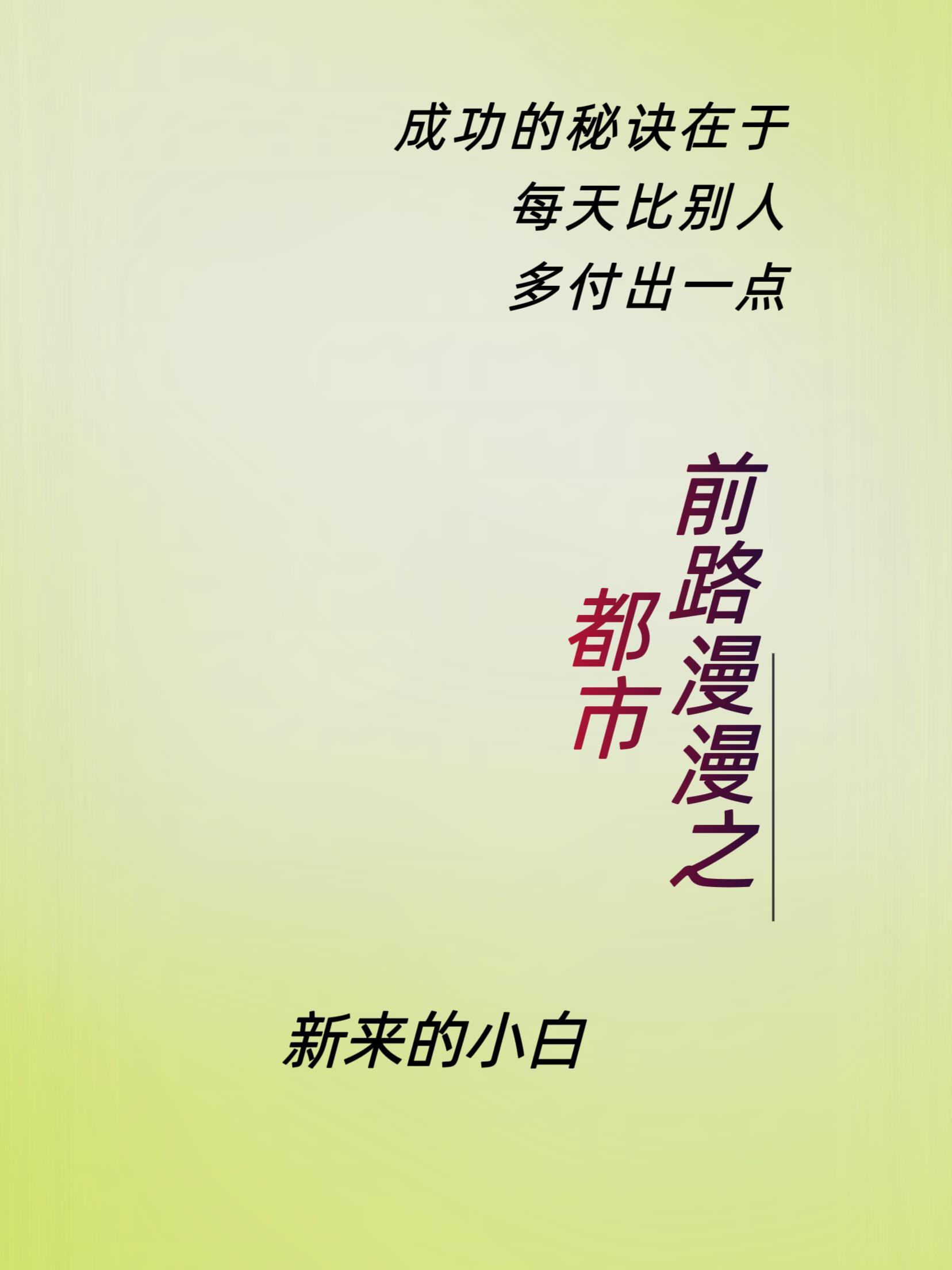69书吧>鱼目混珠是什么生肖? > 第54章(第2页)
第54章(第2页)
这句话孟渔听懂了,他脑子嗡的一下,急忙扑出来抬起双臂横在傅至景和蒋文慎中间,仰高了脸否认,“不是,不是的!”
孟渔对蒋文慎的维护无疑让本就在不悦中的傅至景更添火气,他冷笑道:“朕问的是他,用不着你替他回答。”
新帝的脸没在阴暗里,有浓烈的杀意涌动,仿若只要蒋文慎敢表现出一点异心,弑君的大罪名就立刻扣蒋文慎脑袋上,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傅至景方才要孟渔过去,孟渔不动,现在人站到他面前,他也不觉得痛快了,将人拨开,厉声质问蒋文慎,“说啊,十二弟,说你觊觎朕的少君,巴不得杀了朕取而代之,是与不是?”
体内一把无名火在熊熊燃烧着,摧毁着他的理智与冷静。
这五年来,他踩着一堆又一堆的白骨才坐到了这个位置上,心底那点生而为人本该有的柔软和怜悯早就在日复一日的争权夺势里消失殆尽了。
人命在他眼中不过上下嘴唇一碰的事情,他自己都忘记用过多少刑、杀过多少人,区区一个跟他对着干的蒋文慎,难道还动不得吗?
蒋文慎当真被傅至景三言两句激怒,脸上的神情暴烈又狂躁。
自打孟渔和他的母妃死了之后,这座用人肉烂骨堆积起来的皇城再没有人真心待他,他像一只见不得光的夜行动物,日夜苟活在阴暗之处,不让任何人靠近。
一个跛了脚的、行为失常的、无权无势的王爷,活着只会受尽白眼。
他想起九哥离开后,二哥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为孟渔报仇。
心底一个声音驱使着他提着剑冲进了傅至景的寝宫里,“杀了他,杀了他,杀了害死九哥的罪魁祸。”
这句话沉寂了几年,今夜再次在他脑中敲锣打鼓。
蒋文慎瘦削的两颊肌肉绷紧,双眼因为滔天的愤恨微微鼓出来,手背和脖子上的青筋涌动,死死盯着傅至景那张同样被怒火扭曲的五官——他们的眉眼越相似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
千钧一之际,孟渔抱住了盛怒中的傅至景。
犹如一道温泉流淌过傅至景被烈火焚烧的五脏六腑,将他从失智的边缘给拉了回来。
“你不要生气。”
孟渔怯怯地扬着脸,竭力压下眼中的惊惧,露出个有点讨好的笑,“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不要生气好不好?”
孟渔小心翼翼的表情让傅至景的心像被蜜蜂蛰了一下,痛感直钻到最深处去。
蒋文慎也一瞬间梦里惊醒似的,跌坐回轮木椅,因忍痛站立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重逢后,孟渔初次主动地握了新帝的手,求道:“我们回去吧。”
我们——这个词极大地减少了傅至景的不悦,他的唇角微微勾起来,竟真的应了。
孟渔亦步亦趋跟着傅至景往外走,听见蒋文慎喊他,“九哥。”
蒋文慎说:“不要走。”
“我好想你。”
“我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那种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悲伤语气让孟渔忍不住回头。
蒋文慎满面泪水,从轮木椅跌落,半走半爬要挽留他。
一股尖锐的痛意在孟渔的心口炸开来,痛得他走不动道,痛得他明明还不知道过往,却爆出悲恸至极的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傅至景被他吼得愣了下,“你是不是记起什么了?”
孟渔剧烈摇头,泪水滚滚而落,反复呢喃着“我不知道”
。
傅至景顾不得太多,将人打横抱起,边往外走边道:“宣张太医到太和殿。”
太和殿此起彼伏的哀嚎声。
原是因今日当差的宫人失职看不住少君,新帝下令皆仗责十大板以作惩戒。
傅至景抱着孟渔抬步进殿,见孟渔愣愣地看着行刑的画面,厉喝道:“别打了,都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