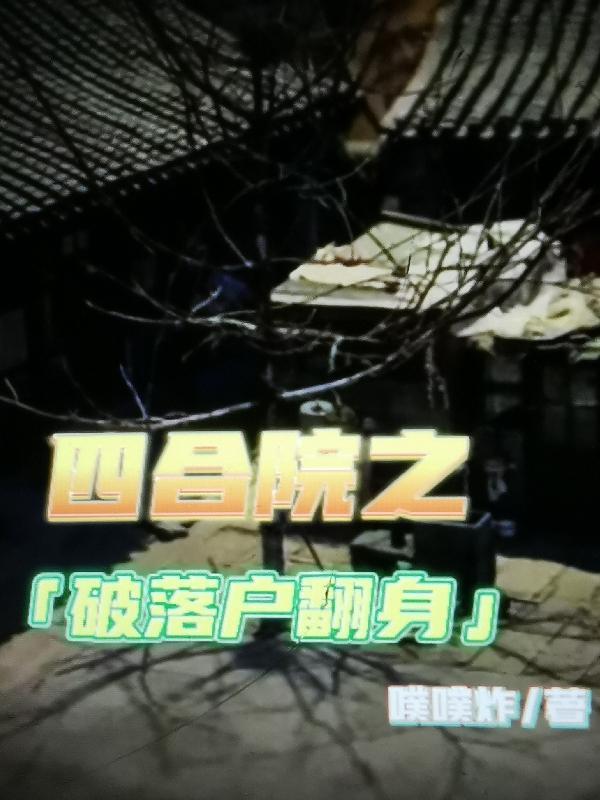69书吧>爱如潮水+他+独行侠 > 第33节(第2页)
第33节(第2页)
“对不起,孩子。”
她黯然地说。
“生你是错,养你也是。”
更多的话没有了。
惨白灯光下的顾慎如像雪人一样冻住了,浑身颤抖,发出簌簌的落雪声。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她的生命好像停在这一秒钟。
与此同时,急诊室外人突然多起来,其中有刚收到消息就赶来的吴教练,以及吴教练特别托关系请来的几位会诊专家。陆别尘补完挂号回来又去那边旁听会诊。专家中有他曾经的导师,都是熟面孔。
很快,又有护士来通知家属将孟廷移动到临时病房,然后办护理证。吴教练闻声迅速地去办了。
一时间,没有人注意到蜷缩在急诊室角落里的顾慎如,直到稍后梁芝赶过来,借了一台轮椅磕磕碰碰进来接她。
但这时候顾慎如已经不在那里了。
梁芝来回蹿着找了一圈都找不见人,突然冲到孟廷那边神经质地大叫一声:“啊呀,她不会也想不开吧!”
她当然也听说了Jen的事。
她这一嗓子喊得病床上的孟廷猛地一颤,睁开了一直紧闭的眼睛。
一旁的吴教练摸一把光头,瞪眼:“不会说话别瞎说!”
与此同时,和专家团站在不远处的陆别尘也听见梁芝的话,神色一怔,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带起一阵风。另一边守在孟廷床侧的吴教练看见他的背影,表情有点不自然。
。
顾慎如不会“想不开”
,至少她自己这么觉得。
离开医院前,她悄悄察看了被转移到普通病房的孟廷,见到母亲在吴教练的照顾下平静得像睡着了。
她知道不应该一声不响地悄悄离开,毕竟一天之内失联两次不符合她一向的“乖”
。但此时此刻,她有个地方一定要去,孟廷和教练如果知道了,肯定不让。
没有人想得到,顾慎如会在这种时候回到训练基地,溜进晚上空无一人的更衣室,把受伤肿起来的脚从护具中拽出来,塞进冰鞋里,然后踩着冰鞋回到冰面上。
她是在冰面上长大的,现在她要与之告别。
她也想要一场无人打扰的,隆重的告别仪式,就像Jen在冰原上一样。
她穿上一件华美的考斯腾,纯黑色纱料坠满了闪钻。原本是为了冬奥特别定制的表演服,但用在这一刻却命中注定般显得更合适。
她身披黑纱在冰上起舞,悼念的是Jen,祭奠的是自己。
想起刚刚得知Jen罹患抑郁症消息的那天,梁芝在一旁带有庆幸地对她说“你和她不一样”
。其他人大概也都这样想。
其实她很想问他们凭什么不一样。
她明明与Jen有一样的使命和困惑。她们是攀登者,只是触不到顶峰,也看不见后路。
没有后路,没有归途,所以她们最终放弃。
顾慎如在冰面上停了一会儿,胸口快速起伏,吸进冷冽的空气。
她本来想的是滑一次Jen最后的那一套舞,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
很早的时候,她曾和Jen一起接受媒体采访,畅谈各自对人生中的最后一场比赛有什么期待。那时的她们还是两个小女孩子,说话都带着点不谙世事的天真和野心。
Jen说最好的结局就是一个完美的4A,而她摇了摇头,说想要SuryaBonaly式的单刃落冰后空翻。
她是认真的。
那个动作因为极端的危险性早都被奥委会明令禁止了,但在这告别的一刻,她就是想要做一个规则之外的跳跃。
哪怕别人不敢,哪怕一旦失误就是非死即残。
冰面上,顾慎如优雅地开始滑行。
没有音乐,她听见冰刀摩擦冰面的声音,这是从她出生起就刻进骨骼的声音。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将优雅打碎,爆裂般发力,翻飞的衣袖像飘零的鸦羽。
她很快就感觉不到受伤的那只脚了,然后是另一只脚,但她没有停下,也停不下来。
旋转、后退,凶猛地起跳。她要完成她的单刃落冰后空翻,那于她而言是最体面的告别。
在凌空时,她预感到了注定的失败,但她心里是平静的,因为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结局,也是她想要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