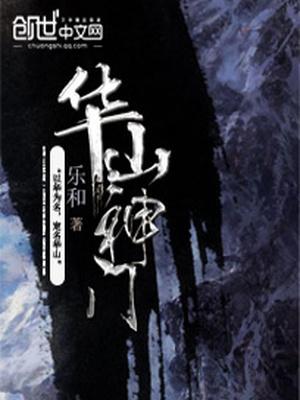69书吧>大兴朝驸马须知晋江 > 第308页(第1页)
第308页(第1页)
她孙媳是个性子暴的,当下把老夫人挣脱了开,徐老夫人提起拐杖来就要打,那夫人一扭身灵巧躲过了,老夫人反倒栽了一个趔趄。赵姑姑手慢没扶稳,徐老夫人仰面栽倒在地上,哎唷哎唷直叫唤。
她生得虚胖,好几个人扶都没扶起来。
孙大夫气得胡子一翘一翘的,让药童背起医箱就走,只留下一句:“老朽医术不精,老夫人另寻高明吧。”
徐老夫人躺在地上哀叹:“家门不幸啊!”
她那孙媳嘴皮子一掀,露出个十足讽刺的表情:“可别装模作样了!我可不是任你揉搓的软柿子!你这孙子残了腿我瞧着都磕碜,若不是模样周正我嫁他干嘛?如今还是个不顶事的,白送我都不要!老夫人咱当初可说好了,婚事不成嫁妆得给我退一半。”
见老夫人气得喘不上气,她又笑说:“孙媳心眼儿好,剩下那一半嫁妆您留着再给您孙子讨房媳妇吧!看看哪家姑娘能给这不顶事的残废下个金蛋出来!”
“滚!你滚!”
徐肃一脸羞愤欲死的表情,拎着她后襟把人丢出了门外。
徐老夫人一头冷汗,多少年怀揣着的金孙梦飞跑了,又被这牙尖嘴利的夫人气了个不轻,当天晚上便不省人事,口眼歪斜,话语不利索。
赵姑姑连夜请了个大夫来,说是中风瘫痪了。
徐老夫人右半脸不由自主地抽|搐,还死死抓着徐肃的手想要说话,咿咿呀呀没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四年前,朝中时局动荡,那时方老爷子焦头烂额,没空操心方筠瑶的婚事,只交代给大儿媳。方家大夫人是跟老夫人一条心的,她给方筠瑶挑的几个都是歪瓜烂枣,什么死了三房媳妇的,莺莺燕燕住了一个院子的,娶她过去当妾室的……
方筠瑶心中不满,听说荣奉伯府的公子在说亲,便自己找了个野路子的媒婆上门说亲去了。
历来这般人家说亲都是找的官媒,没父母之命就上门的这不叫说亲,这叫自荐枕席。伯府也没嘲讽,好声好气把人请了出来,方家却是又一回丢了个大丑。
方老爷子气得不轻,差点把方筠瑶撵出家门,被她苦苦哀求了三天才勉强消火。谁知那个伯府公子不知怎的竟瞧上了她,隔一日带些礼上门。方老爷子也就当睁只眼闭只眼,给她备好了嫁妆赶紧嫁出去拉倒。
谁曾想这伯府公子也不是个好的,一次在园子里前院偶遇方家的七姑娘,出言轻薄了两句,七姑娘哭哭啼啼去找方老爷子做主了。
这七姑娘是方家大夫人的女儿,女儿被人言语轻薄了,大夫人自然气不过。方筠瑶竟还在一旁帮着说和:“七妹妹今年十九了都没许人家,不如与我一起嫁给郎君作伴?”
听了方筠瑶这话,大夫人恨不得撕了她。七姑娘脸皮薄,听了这话更是羞愤欲死,竟一时想不开要去跳井去。
方老爷子再不能忍,将方筠瑶并上那伯府公子一并撵了出去,再不许她进门。
伯府公子丢了个大丑,悻悻走了。方筠瑶把人没留住,又去方家大门求,门里出来两个早有准备的大力嬷嬷一人一边钳着她上了马车,丢去了京郊的一个尼姑庵。
“爷,清音寺到了。”
徐肃给那脚夫付清了银钱,站在寺庙的石阶之下仰着头望向庙门,十几个矮阶之上,有一个三人宽的寺门,墙上的白漆斑驳脱落,左右边各写着“阿弥”
“陀佛”
四字,寒酸极了。
徐肃一时有些想不通,在边关的几年她受了些苦,却也从没过过这般清贫的日子,怎么偏偏挑了这么一处地方。
这些天徐肃本来没想起她来,若不是老夫人成日口齿不清地念叨“丧门星”
,徐肃都快要忘了方筠瑶了。他去方家一打听,守门的家丁告诉他六姑娘生了恶疾,治不好,主动来这尼姑庵吃斋念佛。
寺里空寂无人,香火也少得可怜,功德箱大喇喇地摆在院子里,连个看的人都没有。徐肃走了好一会儿才瞧见两个正在洒扫的尼姑,连忙上前问:“敢问这位……师太,可知一位方姑娘在何处?她叫方筠瑶。”
年长的那位尼姑停下扫帚,合掌行了个礼,淡声道:“出家之人,一律不问前尘旧事。贫尼连自己的俗家名讳都要忘了,哪还记得旁人的?”
徐肃一噎,蹙眉想了想,“她是三年前被人送来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模样生得不错。”
年长的尼姑还在思索,年幼的那位已经想明白了,诧异道:“你问的是那个疯姑子?”
清音寺说是寺,其实只有前后两个四合院,尼姑把他领到了最角落里的一间屋子,远远就站定了,好像里头有什么不干净似的,半步都不想走过去。她伸手给徐肃指了指,“就是那儿了。”
徐肃深深吸了口气,推门而入。推门时带起的一阵灰土在空中飘荡,墙角的蛛网重重叠叠结了好几个,白乎乎一片。
方筠瑶缩在床上编花绳。寺里没闲人伺候她,她一身脏污,唯独一双手洗得干干净净,手中的花绳也没沾上半点灰土。她的手比过去糙了好多,大概记性也不太好了,总是编错,时不时就得拆开重新来过。
这花绳是乐儿小时候最喜欢的,边关的新奇玩意少,以前方筠瑶就常编花绳哄女儿开心。
徐肃站在她身后静静看着,一时心头涌上千般滋味。
曾经两人一起逃过兵荒,五年的边关苦寒也熬了过来,那般艰难的日子都撑下来了,说过的海誓山盟也都是真的。可怎么短短几年,他们两人就过成了这般模样呢?
徐肃启唇想要喊她,“瑶儿”
两字堵在喉中怎么也喊不出来,早没有过去的亲近了,怎么喊都不对味,只轻轻咳了一声。
方筠瑶听见动静回头一看,手里动作顿了顿,若无其事地继续编花绳,低着头不看他。
可方才那短短的一顿已经叫徐肃看出了不寻常,徐肃心里一跳,忙问:“你没疯是不是?”
方筠瑶轻轻吸了口气,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苦笑道:“时好时坏的,指不定什么时候疯半天,寻个门撞两下脑袋就好了。”
徐肃哑口无言,两人静静对视半晌,他低声问:“你后悔吗?”
方筠瑶诧异地看他一眼,似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嗤笑一声:“后悔什么?后悔当初去攀附你?可我当初若是没跟你,那兵荒马乱的,我怕是要做一辈子的军妓了。有什么好后悔的?”
见徐肃怔怔不语,她又轻轻一叹:“我这辈子命苦,没爹没娘没家,什么都没了,只能自己求,没求来我也认了。”
“徐肃,我跟了你五年,最后只求你一件事。”
方筠瑶坐直身子,面容沉静,徐肃甚至想不到她疯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你把乐儿好好养大,嫁妆在老头子那儿,那是他先前许下我的嫁妆,我全留给乐儿。老头子脸皮薄,你上门去求个两回,他会把嫁妆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