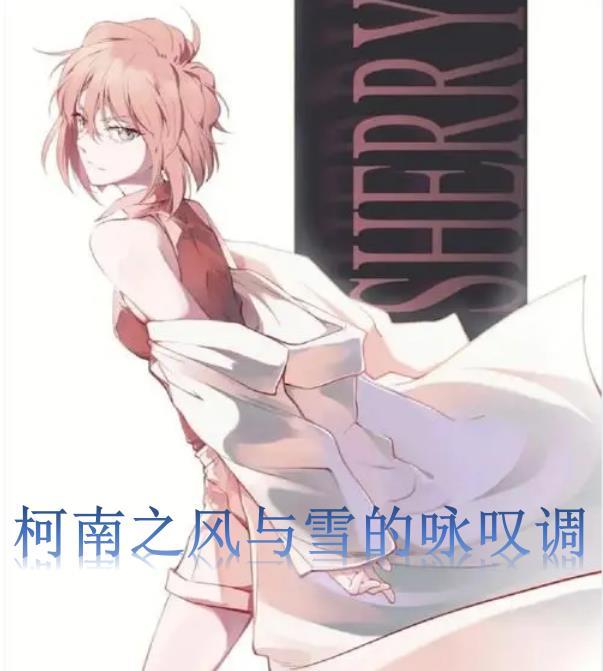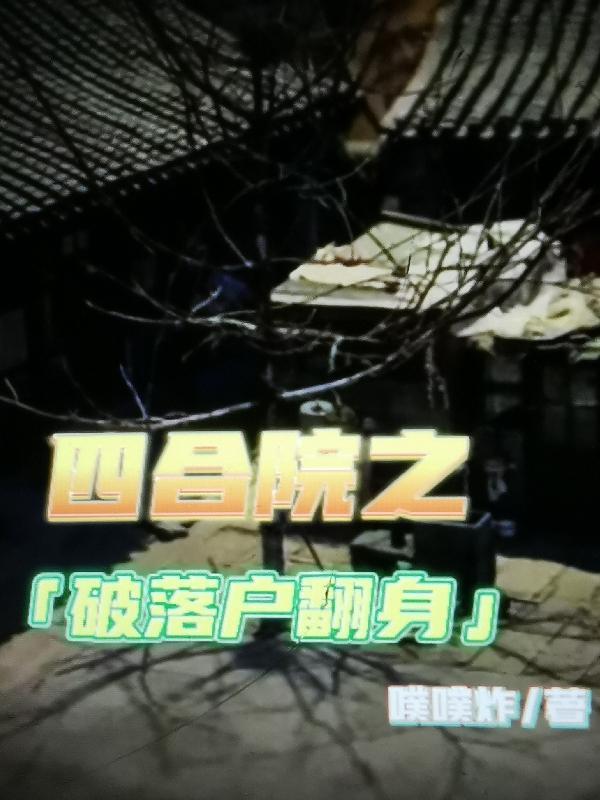69书吧>重生之血色浪漫宁远 > 第98章 升米恩 斗米仇(第2页)
第98章 升米恩 斗米仇(第2页)
钟跃民回过神来,笑了笑。“媳妇儿,你安排就好,咱家的事儿你做主。张莉,以后家里就辛苦你了。”
张莉有些拘谨,情绪不太稳定。“哥,你、你客气了。我也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帮上忙的地方,我尽量。。。。。。”
张莉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周晓白安慰道。“张莉你哭什么呀?那样的男人没什么好留恋的。你也看到了,我和跃民两个人都挺忙的,正好你们你帮我们照顾一下家。”
钟跃民看到后心里也不尽的感慨,这个年代女性的地位还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离婚的女人仿佛成了社会的弃儿,被指责、被唾弃,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
在这个年代,离婚的女人仿佛被贴上了“失败者”
的标签,她们被剥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被剥夺了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她们被迫忍受着别人的议论和嘲笑,仿佛她们的离婚就是一场罪恶。
这年头离婚,不管谁对谁错,都是女人的错,女人离婚是要被看不起的,说话都要小声。就算这样,还是禁不住人家背地里嘴碎,你看这种女人活该没男人要。
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带来了观念的更新与变革。再过2o年,哪怕是1o年,女性再也不用畏惧离婚的标签,她们敢于理直气壮地喊出。“爱他妈能过就过,不能过老娘跟你离婚!”
这种声音,不仅是对过去束缚的反抗,更是对未来自由的向往。她们不再满足于成为附属品,而是寻找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伴侣,不论他是白马王子,还是骡子。
夜色朦胧,张莉坐在木椅上,她的脸色苍白,犹如一朵凋零的花朵。她的头散乱,遮住了那曾经光彩照人的杏仁脸。她用手中的袖子擦拭着红肿的眼睛,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周晓白坐在她对面,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孩,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同情。她知道张莉的经历并不容易,这个看似坚强的女孩,其实内心早已千疮百孔。
张莉用袖子擦拭着红肿的眼睛,声音颤抖地对周晓白说。“姐,他就这么不要我了,我心里不好受。”
周晓白轻轻握住她的手,试图给予她一些安慰。
周晓白又轻轻地揽住张莉的肩膀,低声安慰道。“张莉,别哭了。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再哭也解决不了问题。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张莉点了点头,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抽泣着说道。“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身无分文,那个男人一走,我连个依靠都没有了。”
张莉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和我哥是好人,可说句实话吧。他是我们村的知青,我当初跟他结婚,我爹妈都是死活不同意的。后来他回了城,我两年没他消息,也是自己死不要脸的找来的。我爹妈可是气坏了。你说我现在都离婚了,我再回去,哪怕我爹妈打不死我,我自己也没脸见人啊!我爹妈更没有脸见人。我是万不得已不能再回去的。”
周晓白听到愣了一下,还是自己太冲动了,这是要赖上自己吗?可又不好不管人家,见她还是一个劲的哭,又烦躁的摆摆手。“行了,别再哭了。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就你那男人那样,说实话,真配不上你。他能找到你当媳妇儿,那是他祖坟冒青烟了。你放心的在这住着,帮我妈带孩子。过几年你要是想去工作,我让钟跃民给你介绍一个。”
张莉听了这话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只得慌忙说道。“姐,你放心,我每个月给居委会厂子糊纸盒,每个月有4块钱呢,够我自己吃喝了。”
周晓白问钟跃民。“咱们一个月给张莉多少钱合适?”
钟跃民思考了一会儿。“一个月1o块钱吧!”
周晓白还想说什么时候,张莉赶紧站起来,向钟跃民道谢。“哥,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干。”
张莉就这么在钟跃民家做起了保姆的活。
深夜,月光透过窗帘洒在钟跃民的卧室里,一切都显得格外宁静。周晓白坐在床边,眉头微皱,轻声问道。“跃民,我们给张莉的钱,是不是少了点?”
钟跃民靠在床头,嘴角勾起一抹嗤笑,调侃道“少了?我的媳妇唉,您这要求可真高。您瞧瞧这北京城,您就是找遍了大街小巷,也找不出这个价来。您看看门口的环卫工人,没日没夜地忙,一个月也就挣那么五块钱;再看看那些进城的外地工,一天也就七八块钱,还得拼命干。”
他顿了顿,继续道。“再说了,我们给张莉的已经不少了。你这一来就给那么多,要是惯坏了她,以后怎么办?升米恩,斗米仇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