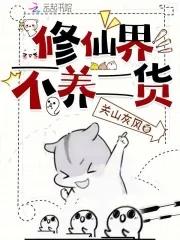69书吧>忍界传说是什么 > 第16章 避难所3(第1页)
第16章 避难所3(第1页)
谁也不知道殴打是缘何生的。
那个壮汉操着乐州口音,手里拿着酒瓶,浑身散着戾气。
没人敢靠近他。
医生抱着自己的头,任凭对方殴打。他的手里拿着药罐,护着身后的人——金碧眼,是个帝国女性。奣认得她,在学校当外教老师,还挺受学生欢迎的。
她蜷缩着身子,泣不成声,显得相当落魄。身边的孩子正在给她递纸巾,也是金碧眼。十岁不到,个子小小的模样,嘈杂的声音似乎影响不到他。注意到医生送来的药罐时,他很是乖巧地接下了。
在公国的人海中,他们就是异类。
奣站在人群中,不由得想着。
那个乐州人满嘴詈语,满脸酡红。乒乓一声砸碎了喝空的酒瓶,将破碎尖锐的部分对准医生。
“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个帝国女人是你什么人,要这么护着她。你让不让?!”
“我不让!她受伤了,我有义务救治!”
这叫乐州人更加来气,往医生身上啐了口痰,利刃甚至划伤了医生的手臂。围观的群众纷纷后撤,不仅没有制止,还说着流言蜚语中伤医生和外教老师。
奣有些看不下去了,即使三个朋友后续赶到,一把拉住了自己也没用。殴打人,什么时候成对的事了?
抽出卷纸,回想之前的感觉,于是卷纸的表面覆盖上一层纯绿色的薄膜。缠住对方的手,夺下酒瓶就好。小腹在烫,血液在流转,奣隔着人群向乐州人甩出卷纸。
就和自己想象的一样,飞离的那一端缠住了乐州人的手腕。奣顺势一拉,那人遂向后踉跄了两步。
“谁……谁啊!”
等那人转头看向自己的手时,奣已经召回了卷纸——自己做不出更加精细的操作了。
幸好这时两个士兵吹着哨子,前来疏散群众。看到伤员和醉汉,很快就明白了情形。一个带走医生,一个拿捏乐州人的关节,叫他乖乖放下碎酒瓶。
人群很快散去,独留外教老师和她的孩子在原地。那孩子抚摸着母亲的头,环顾四周找着什么。最终他的视线停在了自己的身上,叫奣有些意外。
那双碧蓝色的眼睛充满了稚气和天真,妹妹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那眼神中还有着一种奣说不上来的感觉。男孩向奣走去,不紧不慢,不卑不亢。
“谢谢哥哥。”
“不用谢。”
稚嫩的声音,短短的一句,配着不是非常标准的帝国礼。然后羞涩地笑着,奔回到母亲身边。
条件反射性地回了一句,可究竟是为了什么感谢自己呢?
就算赶走了醉汉,母子两人是异类的事实仍然不会改变。
就在过去的几分钟里,饱餐一顿,准备返回自己帐篷的普通人无视他们,埋头扫地的清洁工无视他们,路过的政府官员无视他们。
奣一步未动,一如方才的人群尤在。自己只是制止了救治过自己的医生被无端殴打,可换来的却是帝国人的感谢。
明明现在最想做的是参军,只有参军才能名正言顺地反击敌人……
奣很纠结,可朋友们并不给自己这个时间。
“刚刚那个咻咻咻的,是什么啊?真帅!”
最先问的是董琪,任和则一把抓住了奣的右手,撸起袖子,露出护腕。
“你这个不会是纸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