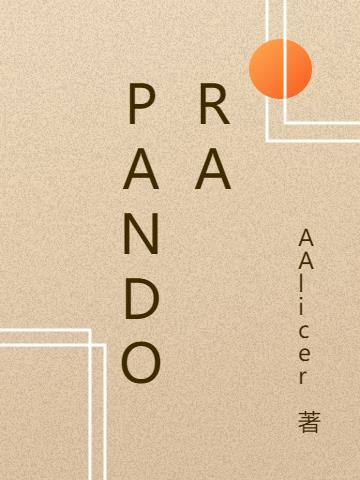69书吧>离朕皇陵远亿点txt笔趣阁 > 第三章(第1页)
第三章(第1页)
欺君罔上的逆臣闻言非但不恼,反而轻轻笑了起来。
“臣入城前,听闻陛下受奸人蒙蔽,误解了臣的一片赤诚之心,”
许是体恤赵珩是个半聋,他慢条斯理道:“恐惧之盛,竟到了要饮药自尽的地步,今日得见陛下天颜,方知流言荒谬。”
“陛下胆略过人。”
另一只手顺着赵珩的下颌向上摸去,他指尖上蹭了皇帝方才吐出来的血,沾了血的铁器滑腻而冰冷,在皮肤上留下了一道狭长的红痕。
言辞恭敬,动作却轻慢至极。
被铁甲包裹的手指一路游走,肆意亵渎着他口中的帝王。
被臣下如此欺辱,皇帝但凡有二三分骨气,都无颜苟活于世。
赵珩当然没有——没有骨气。
大昭朝的开国皇帝,在面对着几已占据他半壁江山的逆臣,勉强将自己从起死回生的狂喜中抽出来,喘了口气,慢慢道:“姬将军谬赞。”
他的话音里竟还带着笑。
赵珩想忍,但没忍住。
姬将军居高临下地俯瞰着皇帝,从他的角度看,帝王这幅模样实在说不上有何种威仪,因玉带被解下,皇帝的朝服散乱得不成样子,只要他稍稍低头,就能看到一截被素色里衣遮挡着的腰。
姬将军的视线不着痕迹地向上一移。
看脸,皇帝就更狼狈了。
他之前因靖平军一路穷追不舍,日日夜夜借酒消愁,只待酩酊大醉之后才能睡着,长期纵酒少食,他消瘦好些,眉骨愈显棱棱。
面色惨白,几无血气,皇帝浑身上下所有的血色都堆在了唇角和耳边,不过,是流出来的那种。
此时此刻,他看居然还是乐呵呵的。
亡国近在眼前,皇帝到底在高兴什么?
姬将军几乎为皇帝的没心没肺感到惊异了。
包裹着赵珩喉咙的手掌轻轻一拢,姬将军问:“陛下在笑什么?”
他用的力气恰到好处,足够赵珩不被憋死,但每吸一口气都艰难得要命。
赵珩无神的眼珠转了下,目光在扼着他喉咙的手上一闪而过。
“朕在笑,”
赵珩道:“姬将军果然青年才俊,今日朕见将军,开怀之至,难以,”
他咳嗽了一声,唇角渗出一片黑红,“掩饰。”
疼痛如丝刃,细密缠绵地裹住了赵珩的五脏六腑,随着他呼吸起伏间,切入身体,割得皮肉散落,鲜血淋漓。
赵珩疼得小指蜷缩,面上的笑容却有增无减。
污血顺着嘴角淌下,从下颌到脖颈都染得黑红。
皇帝素日养尊处优,甚少出门,生得比寻常男子白好些,加之中毒失血,未遭血液濡湿,裸露在外的皮肤白得几乎透明。
浓艳的红黑两色间,偏偏生着一截雪白的脖颈。
脖颈纤细,大半被扼住,铁器碾着肌肤,在边缘了压下道道带着花纹的淤红。
倘他想,只需再用一点力,就能生生掐断皇帝的颈骨。
姬将军俯身,在皇帝耳边道:“好……”
好什么?
声音极轻,赵珩听不见。
一缕热气拂过耳垂。
赵珩不适地皱了下眉。
先前喘气冷得像个死人,突然活了,让人免不得震悚厌恶。
“那陛下,”
姬将军问:“可想再开怀些?”
掌下脖颈浅青色的血管因疼痛贲鼓,可怜兮兮地跳动着,长指一搭,姬将军刻意碾了两下,仿佛能感受到下面汨汨流淌的鲜血。
赵珩不想都知道此逆臣贼子绝对说不出什么好话,断然拒绝,“不必,朕见到将军已是欣悦至极,乐极生悲,朕……”
手指施力。
赵珩有气无力地咳了声,朝姬将军吐了一小口血。
心道你不让朕说,还装模作样地问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