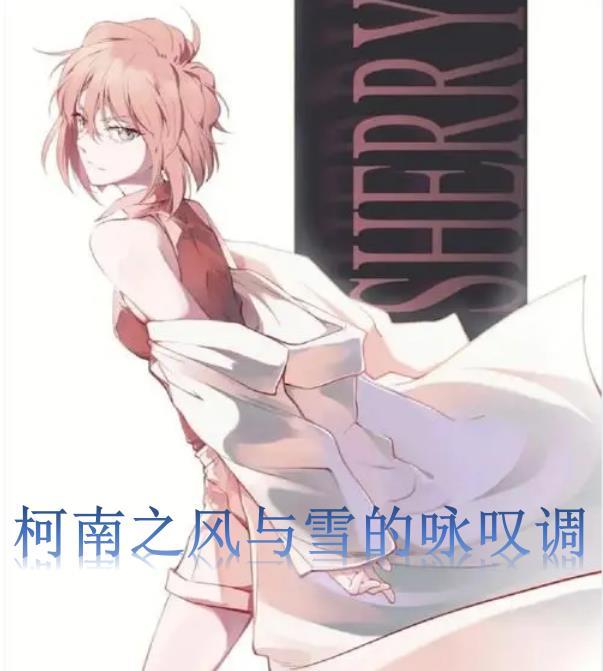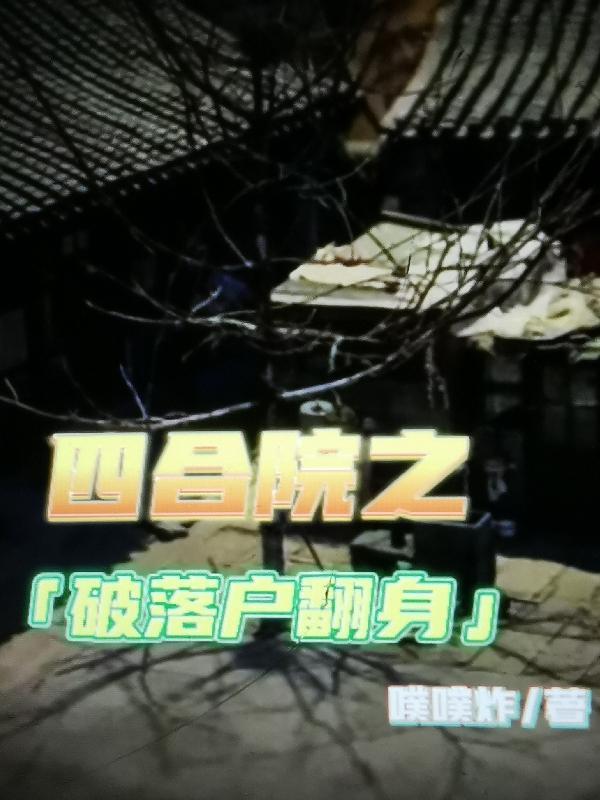69书吧>娇娇在上笔趣阁免费阅读 > 第76页(第1页)
第76页(第1页)
话音未落,门前一道匆忙的身影赶来,一见晏明月忙阻拦道:“民妇见过王妃,苏太医交代王妃还需好生修养,还请王妃快快回榻上,苏太医马上就来。”
晏明月脚下步子一顿,上下打量一番来人,却并非认识之人。
面前的女子面容清秀,瞧着岁数不大,有股子小家碧玉的感觉,但身着清雅淡朴,又自称民妇,晏明月微蹙黛眉,问道:“你是何人?”
女子后退半步垂头恭敬道:“民妇林氏,家夫与王爷此前有些交情,听闻王爷今次要前去东岭为老夫人贺寿,这便邀约了王爷顺道来淮安小聚,只是没想到途中会……”
淮安。
晏明月忆起贺凛所说在淮安的老友,那眼前这位便是他的夫人了。
但晏明月此时无心寒暄,浅浅看了林氏一眼,快声道:“本宫并无大碍,王爷此时情况如何,本宫想去看看王爷,不必再传苏太医,还请夫人带路。”
林氏犹豫了一瞬,显然有些为难,也不知是在担心晏明月的身子,还是在担心叫晏明月瞧见贺凛的情况。
踌躇片刻,也当知晏明月心系贺凛,哪能当真安心躺下,见她似乎并无什么大碍,这便松了口:“王妃这边请。”
一路跟着林氏绕过小院,这里应当是这位老友的府邸,不算阔气,但也沁心雅致,快步走到院门前,一名陌生男子正和北风在说着什么。
被绑前的记忆涌上头来,晏明月当即怒了眼眸,大步上前,还未开口北风便先一步双膝跪在了晏明月面前:“王妃,属下罪该万死,是属下办事不力,王妃要责要罚,属下绝不会有半句怨言。”
话末,向来刚毅挺拔的北风尾音似乎还带起了哭腔。
一旁男子忙上前半步,躬身向晏明月作揖解释道:“王妃莫怪,在下岳廷安,乃王爷旧识,此次一事还未能全数排查清楚,但请王妃莫要怪罪于北风,那奸臣使了易容之术,先后化作北风和银翠的模样骗过了守卫,这才叫事情陷入难局之中。”
跟在身后的银翠闻言也站了出来:“是啊王妃,奴婢被那人绑在草垛后面,亲眼瞧见那人化作了奴婢的模样,骗了其他下人,还明目张胆将您掳走,若要怪,便将奴婢一并责罚了吧。”
易容术。
晏明月眉心突突直跳,她那时分明察觉有些不对劲,可到底是没了那防备之心,可疑的草垛也未曾细看。
是她的大意害此事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又怎可去怪罪旁人,况且也不是他们的错。
晏明月沉重地闭上了眼眸,而后再睁开,眼底一片深幽,抬手扶起跪地不起的北风,沉声吩咐道:“备些热水,本宫去看看王爷。”
说罢,晏明月伸手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屋内静谧无声,晏明月进屋便瞧见了那个趴在床上背部朝上的身影,一动不动趴在床榻上,甚至连微弱的呼吸也感觉不到,就像是没了生命体征一般。
晏明月心下一惊,面色顿时难以再保持平静,连忙上前几步,伸手探上贺凛的鼻息,才缓缓松了口气。
他只是太虚弱了。
心像是被什么揪紧了一般,晏明月视线落到贺凛已经被处理过的背部,药草铺在伤痕上,密密麻麻一片,已没有了出血的迹象。
应是除了伤势还未来得及整理别的,侧趴着的脸庞上血和污泥混杂在一起,还有被黑烟烧过的痕迹,将他脸庞早已折腾得再无半分原本的俊美可言。
狼狈得,令人无法将他与他平日里矜贵淡漠的模样结合在一起,他总是沉冷的,稳重的,眼神里有时会带着与他年纪不符的嚣张气焰,有时又会带着划破冷冽的炙热。
只是如今,却痛苦地将眼眸紧闭,抹不开浓雾的剑眉微微皱起,像是沉睡中也在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痛楚。
晏明月看得心头一阵刺痛,转头便见银翠已匆匆忙忙将热水和毛巾备来了。
晏明月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心绪平稳了几分,这才上前接过银翠手中的东西,轻声道:“你先退下吧。”
晏明月声音很轻,语气很淡,令人听不出情绪。
银翠一愣,看了眼屋中趴着的身影,心底一酸,抿了抿嘴不再多说,很快退出了屋中。
晏明月隐约听见屋外刻意压低声音的谈话声,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她也无心去细闻。
挽起袖子露出一截葱白的小臂,温热的水在上方冒出层层热气,伸手探进热水中浸湿了帕子,缓步走到贺凛床边坐了下来。
血和泥污擦去后,他本身立体俊美的五官便再次显露了出来,只是苍白的脸色和干涩的唇让他仍是显得虚弱不堪。
浓密的眼睫微颤着,像是在诉说他的痛楚,他本该是姿态高贵,冷血睥睨的模样,眼下却因为她,显得十足可怜,再无半分气势。
晏明月收回眼神,在热水中洗净了帕子,清澈的水顿时晕开深重的血色。
除却背部的伤势,手臂和腰侧也有不少烧伤红肿的迹象,心下不由想到当时大火缭绕的场景,他究竟是何来的勇气,竟就这么无所畏惧地冲了出去,他就不觉得疼吗。
眼眶止不住地酸,晏明月指尖细细抚过那一片血肉模糊的伤口,肩胛处一道深长的伤口终是落入了眼中,但晏明月却全然想不出这是他何时所伤。
前些日子他们朝夕相处,贺凛因着解毒,连下床都难,又怎会遭此重创,如若不是这伤,兴许此次还不会落得如此艰难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