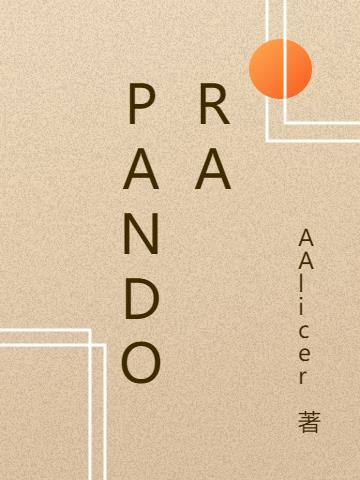69书吧>和富豪在梦里养鸟养儿子 轻松 > 第6页(第1页)
第6页(第1页)
在杜晓眠的记忆里,杜晓率那个倒霉蛋子三岁那年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留了一身疤痕,刚出院时,脱了衣服,背上、腿上,屁股上全是狰狞的、凹凸不平的,足足成年人手指厚的疤,并且,腿还瘸了一只,虽然不算太严重,但走路时,尤其是跑得快时,总会失衡,异于常人。
父母因为心疼他吃了太多苦,打不得,骂不得,纵容他长成了一只动不动就炸毛的猫,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后来又迷上打游戏,泡在网吧里整天整天不着家,也不知道继续下去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公害。
杜晓眠一直觉得,那小瘸猫要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在学校里不被同学们排挤嘲笑,大概也会长成一个斯文儒雅的美男子,毕竟那张脸是从小帅到大的。
但是现在,眼前那两根小短腿儿迈得飞快,却一点跛的迹象也没有。
唯一的解释就是,杜晓率的腿没有受伤。
难道自己成功阻止了四年前那一场爆炸?
杜晓眠手在脑袋上敲,除了脑仁痛,什么也想不起来。
她头重脚轻回到堂屋,黎溯川和张翠花已经吃完早饭,而虫儿和舅舅小姨坐在地垫上玩。
杜晓率在‘大侄子’羡慕得流口水的目光下,两口肯完雪糕舔干净棍子扔到一边说:“雪糕是冰的,你不能吃,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好玩的?”
说着献宝似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只绿油油亮晶晶的虫子出来:“金龟子!舅舅费了好大力气才抓到的哦。”
杜晓蕊坐在旁边却不敢靠近,又怕又嫌弃地说:“幺弟你好恶心哦,拿虫子给虫儿玩,把他吓到了怎么办?”
结果话刚说话完,一只胖乎乎的手爪子抓过杜晓率手里的虫子往嘴里塞。
“哎!吃不得!乖乖耶,你还没开荤,不能吃肉。”
张翠花抓住虫儿的手吓得花容失色,杜晓率赶紧把宝贝抢回来:“这是虫子,不能吃的,这是拿来玩的。”
虫儿被抢了‘零食’不高兴,又伸出另一只手去抓,杜晓率生怕宝贝被吃了,重放里裤兜里藏好,特无奈特无语地说:“这是虫子,真的不能吃啊,要不舅舅给你找点别的玩吧,我们去喂鸽子好不好。”
但虫儿不依,抢了两下没抢到,嘴巴一撇,哇啦啦地哭起来:“啊啊啊……啊……嘛嘛……啊……”
杜晓蕊见状气冲冲地瞪杜晓率:“都怪你,把虫儿弄哭了吧,我要回家跟妈妈告你。”
杜晓眠站在堂屋门口止步不前,看着里面的人和动静,像在看一场热闹的电影,明明跟自己息息相关,但里面的人却又好像都不认识。
甚至连老三老四都很陌生。
在她的印象里,杜晓率从小到大都是个闷葫芦,整天拉着个脸,对谁都爱理不理,哪会像现在这样趴在地上,撅着个屁股哄小孩儿开心。
杜晓蕊呢,明明是个女孩子,却把自己活成了糙汉,别说怕虫子,连蛇都敢抓,甚至还会在杜晓率跟人干架时,拿起砖头追着那些欺负杜晓率的人骂。
杜晓眠看着看着,渐渐地视线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张翠花的哄声:“哎呀,我的乖乖耶,那是虫子啊,哪里能吃哦,难道你要吃自己亲戚呀,不可以的哦,同类不能吃同类哦。”
虫儿越哭越委屈,趴进张翠花怀里要抱抱,张翠花心痛万分:“哦哟,乖乖莫哭啊,太婆手疼抱不动你了,让你妈妈抱啊,晓眠,你过来抱抱虫儿呢。”
杜晓眠闻言,慢慢走过去,却不是抱虫儿,而是抓起杜晓率的胳膊一声不吭往楼上房间里拉。
“哎,哎!晓眠!小四儿还小,又不懂事,你怪他干啥呀。”
张翠花急了,回头冲黎溯川使眼色:“川娃儿,你上去看看,莫让她把小四儿打了。”
黎溯川自始至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像是对这样的闹剧屡见不鲜:“没事儿,放心。”
然后他抱起虫儿:“走,爸爸带你喂咕咕。”
虫儿立马破啼为笑,嘟着嘴叫:“咕咕,咕咕,咕咕。”
杜晓蕊兴奋地跟在他们身后:“川儿哥,我也要跟你一起喂咕咕。”
黎溯川:“走嘛。”
楼下的吵闹声被关在了门外,杜晓率望着杜晓眠苍白的脸色,识地道歉:“姐姐我错了,我以后不给虫儿玩虫子了。”
杜晓眠盯着那张白白净净、眼珠子溜圆的脸蛋,半晌之后才深吸了一口气道:“手举起来。”
杜晓率乖乖举起手,眼泪花打转:“姐姐我真的错了。”
杜晓眠伸出手,在空气里僵硬了几秒最终挠起他的衣服。
虽然心里已经有猜测,但一刻得不到证实,她的心就永远悬着。
后背上平整干净,别说疤痕,连一颗痣也没有,她一股作气,顺势连他的裤子也扯了下去,杜晓率吓哭了,小声地求饶:“姐姐我也后再不玩虫子了,你不要打我屁股好不好,昨天妈妈打了,现在还疼呢。”
杜晓眠定眼一看,白花花的屁股上果然还有一点红印。
她心里那根紧绷的弦也随之松了下来。
她把杜晓率的裤子重拉回去,衣服也拉下来,再次盯着他的脸看,俊俏的小男孩儿,眼睛通红,睫毛上沾着泪珠,有点委屈又有点可怜。
杜晓眠忍不住笑了,两只手在他脸上来回搓了两把道:“好了,不打你,不过以后要乖乖听话,在学校不要跟同学打架知道吗?”